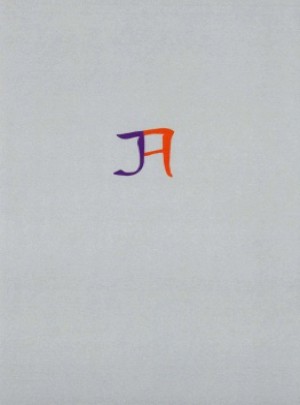引論:我們?yōu)槟砹?3篇藝術(shù)繪畫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chuàng)作。它們是您寫作時(shí)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人們過(guò)去并未意識(shí)到兒童隨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義,更談不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關(guān)注,然而,隨著人類藝術(shù)史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現(xiàn)代藝術(shù)的產(chǎn)生,兒童藝術(shù)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顯。現(xiàn)在,“兒童藝術(shù)”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兒童藝術(shù)中那種形象的簡(jiǎn)化、畫面的和諧、富有表現(xiàn)力的線條、大膽的純色平涂以及那種無(wú)意識(shí)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使得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家懷著新奇的目光從兒童藝術(shù)中汲取營(yíng)養(yǎng)。
二、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大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認(rèn)識(shí)與評(píng)價(jià)
兒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為什么會(huì)吸引全世界藝術(shù)家的目光?在兒童藝術(shù)中,兒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態(tài)每每使我們拍手稱快,是任何人為的方法都無(wú)法企及的。兒童藝術(shù)是無(wú)意識(shí)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是兒童心智和心緒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現(xiàn)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源泉。其構(gòu)圖造型稚拙有趣,似無(wú)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動(dòng)。正如黑格爾所說(shuō):“兒童是最美好的,一切個(gè)別特殊性在他們身上好像都還沉睡在未展開(kāi)的幼芽里,還沒(méi)有什么狹隘的東西在他們的胸中激動(dòng),在兒童還在變化的面貌上,還看不出承認(rèn)繁復(fù)意圖所造成的煩惱,因而在兒童繪畫里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是他們對(duì)事物無(wú)意識(shí)的、天真率直的看法。”兒童藝術(shù)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表現(xiàn)性,注重個(gè)人感受。兒童天性充滿熱情,能主動(dòng)、自由地表現(xiàn)畫面,兒童看世界有他們自己的獨(dú)特眼光,他看起人來(lái),只看到一個(gè)人的一個(gè)大頭,頭上的兩只眼睛,一個(gè)鼻子,一張嘴巴,什么耳朵、頭發(fā)、眉毛,他都沒(méi)有看見(jiàn),所以他不畫一個(gè)人的身體,他看得不重要,只畫一條線來(lái)表示。這些入眼的觀察對(duì)象在兒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鮮明。兒童是畫其所想而非畫其所見(jiàn),因此兒童畫出的作品往往想象豐富,用色大膽,富有生氣,有更多的靈性。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反叛傳統(tǒng),追求單純和質(zhì)樸無(wú)華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兒童藝術(shù),而且給予兒童藝術(shù)以高度的評(píng)價(jià),甚至對(duì)兒童的藝術(shù)狀態(tài)和兒童的藝術(shù)作品崇拜不已。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畢加索曾說(shuō)過(guò):“我曾經(jīng)能像拉斐爾那樣作畫,但我卻花了畢生的時(shí)間去學(xué)會(huì)像兒童那樣作畫。”這在當(dāng)時(shí)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實(shí)這種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新的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在野獸派那里已有所表現(xiàn)。康定斯基崇拜兒童藝術(shù)是因?yàn)樗J(rèn)為兒童藝術(shù)是對(duì)事物內(nèi)在本質(zhì)的直覺(jué)表現(xiàn),他說(shuō):“兒童除了描摹外觀的能力之外,還有力量使永久的內(nèi)在真理處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現(xiàn)的形式中。……兒童有一種巨大的無(wú)意識(shí)力量,它在此表達(dá)自身,并且使兒童的作品達(dá)到與成人一樣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畫家馬蒂斯、杜飛、夏加爾,尤其是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同樣感到了兒童藝術(shù)的魅力。西方藝術(shù)家所向往的那種無(wú)意識(shí)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信手涂抹”在兒童藝術(shù)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三、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與模仿
從19世紀(jì)后半葉起,西方畫壇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眼花繚亂的西方現(xiàn)代畫派,既受到兒童繪畫在藝術(shù)形式上以及表現(xiàn)技巧方面的啟發(fā),更受到兒童對(duì)待繪畫的基本態(tài)度無(wú)意識(shí)的強(qiáng)烈沖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與模仿直接反映在他們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兒童的這種天真狀態(tài),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繪畫技巧上使用兒童那種環(huán)繞的、粗陋的輪廓線,反應(yīng)在作品《動(dòng)物園》、《他喊叫,我們玩》和《女舞蹈家》中,這些畫中線條技法與兒童素描的線條技巧很接近,盡管它更細(xì)窄,更優(yōu)美。《高架橋的革命》畫面上簡(jiǎn)單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橋,表現(xiàn)出了克利對(duì)兒童畫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號(hào)化形象的興趣。在米羅的繪畫世界中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位大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許多繪畫作品中,人物沒(méi)有身體表現(xiàn),頭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腳為末端的直腿上,整個(gè)臉像一個(gè)不規(guī)則的橢圓形或圓形,這種極端單純化的形象的變體,也就是兒童畫中的“蝌蚪人”樣式,如作品《在甲殼下部》、《黎明時(shí)瞪羚的哭叫》和《繪畫》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農(nóng)場(chǎng)》都已呈現(xiàn)出一種兒童般稚拙的風(fēng)格傾向。后來(lái)由于戰(zhàn)爭(zhēng),米羅的作品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畫面依然保持他那種天真、優(yōu)美的風(fēng)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詩(shī)人》都是在戰(zhàn)爭(zhēng)的威脅之下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但我們從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跡。無(wú)怪乎有批評(píng)家說(shuō):“米羅的天才是一種返老還童的天才。”涂鴉和兒童藝術(shù)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靈感來(lái)源,他特別贊同用最簡(jiǎn)單的正面和側(cè)面形象及兒童的輪廓線風(fēng)格畫出大腦袋粗陋人物,也贊同兒童對(duì)記憶中傳達(dá)信息的細(xì)節(jié)的強(qiáng)調(diào),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蠻、直接和確定的方式拋棄“后天學(xué)到的手段”,去探討一條回到“藝術(shù)基本的、形成的時(shí)期,記錄下兒童式的天真與好奇狀態(tài)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畫面中描繪的是巴黎的景色與生活,具有一種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擺脫了克利藝術(shù)中那種幻想、略顯天真的氣質(zhì),而轉(zhuǎn)向一種獨(dú)特的、奠定自己在藝術(shù)史上地位的繪畫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出一些涂鴉形態(tài)的作品,如在《人間的聯(lián)歡節(jié)上》,我們可以看到的一種以此法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令人厭惡和不安的歡樂(lè)氛圍。
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性與兒童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是一致的。“荒誕藝術(shù)比起優(yōu)美、崇高的藝術(shù)更加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nèi)在生命力。”這是西方現(xiàn)代畫派對(duì)怪誕藝術(shù)的看法和推崇。現(xiàn)代派大師馬蒂斯、畢加索等人就從古代非洲的繪畫和雕塑中吸取怪異而又荒誕的特點(diǎn),在我們的眼中極不符合常規(guī),但這與兒童美術(shù)中的無(wú)意識(shí)荒誕的想法極為相似。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欣賞他們的天然和單純,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國(guó)評(píng)論家在觀看他們的畫展時(shí),曾稱這些顏色不符合“客觀實(shí)際”,藝術(shù)形象難以理解。雖說(shuō)在現(xiàn)在看來(lái)有點(diǎn)言過(guò)其實(shí),然而的確在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畫家進(jìn)一步轉(zhuǎn)向表現(xiàn)內(nèi)心情感,這也是近現(xiàn)代以來(lái)西方繪畫逐漸擺脫傳統(tǒng)上摹寫現(xiàn)實(shí)的主流畫法的新的一步,在野獸派繪畫中,馬蒂斯等畫家的一些人物畫有一個(gè)特點(diǎn),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彎曲的形態(tài)和封閉的輪廓線。如馬蒂斯的《浴者》和《海濱婦女》,這些作品使人想起兒童藝術(shù)的某些特點(diǎn),人物的形象看起來(lái)“不準(zhǔn)確”。上述這些對(duì)兒童藝術(shù)語(yǔ)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個(gè)方面,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那里重新獲得天真、純樸和清新的內(nèi)在品質(zhì)。
四、現(xiàn)代主義繪畫大巧若拙
現(xiàn)代主義繪畫在許多方面更借鑒兒童藝術(shù),但他們的目的并非簡(jiǎn)單地重創(chuàng)兒童繪畫,在技巧、表現(xiàn)形式上與兒童繪畫有很大差別。兒童繪畫是在生命之初對(duì)世界的探索嘗試,表達(dá)的是整個(gè)生命尚未展開(kāi)的天性。而大師的繪畫則是在生命成熟階段對(duì)探索世界的提煉總結(jié),表達(dá)出整個(gè)生命發(fā)展過(guò)程凝結(jié)出來(lái)的人格特征和藝術(shù)個(gè)性。所以,兒童畫一張張來(lái)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積看起來(lái),其面貌給人的感覺(jué)大同小異。大師繪畫則不同,都具有獨(dú)一無(wú)二性。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現(xiàn)代畫家在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藝術(shù)個(gè)性,他們使用兒童的符號(hào)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們比其他藝術(shù)家更需要這種敏銳的感覺(jué)力,帶著激情去感受兒童的繪畫世界。他們的繪畫有著精致的層次和精湛的技巧,雖然繪畫的最終效果有著明顯的隨意性,但與兒童天真的藝術(shù)并未完全融合,保持著各自的獨(dú)立性,又相得益彰。兒童的繪畫作品是“原始”形態(tài)的、天真純樸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樣式表現(xiàn)出來(lái)。這在兒童是很可貴的,也是許多中外畫家所追求的藝術(shù)境界。那么藝術(shù)家追求的天真純樸和稚拙與兒童繪畫所表現(xiàn)出的天真純樸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轍呢?這對(duì)于我們更深一步了解兒童藝術(shù)是至關(guān)重要的。審美創(chuàng)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階段。開(kāi)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隨著審美創(chuàng)造技巧的提高,進(jìn)入精巧工巧階段,有了豐富的經(jīng)驗(yàn)、功夫、素養(yǎng),才能落盡繁華歸于樸淡,進(jìn)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沒(méi)有深厚的功底,片面為拙而拙,只會(huì)粗陋低俗。戴復(fù)古說(shuō):“樸拙唯宜怕近村。”(《論詩(shī)十絕》)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則是一種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質(zhì)。拙樸絕非粗率平庸之輩所能達(dá)到的,它是審美創(chuàng)造高度成熟的標(biāo)志。追求兒童趣味的藝術(shù)家在某些方面與兒童繪畫較為相似,例如:以線為主,平涂色彩,不講焦點(diǎn)透視及夸張變形手法等等。但兒童藝術(shù)中的那種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藝術(shù)家們加以發(fā)揮、拓展,成為嶄新的藝術(shù)形式。雖然他們畫中的“拙”與兒童繪畫中的“拙”有著形式上的相似,但卻又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們是老子所說(shuō)的“大巧若拙”之“拙”。寫意大師崔子范也曾說(shuō):“一個(gè)沒(méi)有受過(guò)專業(yè)訓(xùn)練的孩子只憑熱情作畫。在他長(zhǎng)大之后,也應(yīng)該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態(tài),去重新發(fā)掘自己兒時(shí)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畫中表現(xiàn)自己的感情。當(dāng)一個(gè)成熟的畫家運(yùn)用這種方式作畫時(shí),當(dāng)他將藝術(shù)大師的精湛技巧與孩子般的天真爛漫融合在一起時(shí),會(huì)感到極大的快慰。”雖然西方的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畫家的作品源于兒童繪畫的造型符號(hào),但他們靠熟練精深的技巧來(lái)完成。大體上都經(jīng)歷了由開(kāi)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趨精深,進(jìn)而追求“返璞歸真”的過(guò)程。雖然也有追求兒童“拙味”的畫家未經(jīng)過(guò)專門的訓(xùn)練,但他們也難免經(jīng)受藝術(shù)傳統(tǒng)的熏陶,前輩及同代畫家的影響與個(gè)人技巧的錘煉。克利雖曾說(shuō):“無(wú)需什么技巧”,但他畢竟經(jīng)過(guò)了傳統(tǒng)藝術(shù)熏陶,其藝術(shù)風(fēng)格必有傳統(tǒng)技巧的痕跡。可見(jiàn)兒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畫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樸最難,拙近天真,樸近自然,能拙樸則渾厚不流為滯膩。”拙樸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跡,使人不覺(jué)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shí)濃”(《東坡題跋》),在平實(shí)樸素粗散的形式中,蘊(yùn)含著深厚的審美素養(yǎng)和豐富的情感意味。沒(méi)有一定技巧的錘煉,一味片面追求兒童“拙味”,只會(huì)流于粗俗淺薄,達(dá)不到自然渾化的拙樸之境。
五、結(jié)語(yǔ)
總之,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藝術(shù)中獲取到了造型符號(hào)的靈感,同時(shí)也通過(guò)自己的作品和言論促成了人們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進(jìn)一步關(guān)注、承認(rèn)和了解。在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傳統(tǒng)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首先被打破,幾乎沒(méi)有什么尺度可以將兒童藝術(shù)與大師的作品相區(qū)別。當(dāng)然,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家的作品與兒童的繪畫作品之間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劃上等號(hào),這些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的繪畫畢竟是落盡繁華歸于樸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參考文獻(xiàn):
[1]羅伯特·戈德沃特.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原始主義[M].殷泓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1993:54.
[2]阿恩海姆.藝術(shù)與視知覺(jué)[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篇2
自在而富有個(gè)性的線條語(yǔ)言
如果說(shuō)“團(tuán)塊中的精神”的造型理念使奧爾巴赫的作品獲得厚實(shí)凝重的體量感,那么其自在而極具個(gè)性的線條表現(xiàn)語(yǔ)言,就像經(jīng)脈和血液一樣,使其作品充滿了靈性、活力和意韻,各種長(zhǎng)短不一、自由而略帶幾分紊亂的或平直或旋勾的折彎線條與形塊、調(diào)子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其獨(dú)特的語(yǔ)言風(fēng)格。藝術(shù)史上以線造型的大師有很多,但奧爾巴赫的線條充滿著自己的情韻,形成了自己線性語(yǔ)言的編排“密碼”。確切地講,奧爾巴赫的線就像密碼中的亂碼,看似紊亂無(wú)序,實(shí)則明確地勾畫出奧爾巴赫窮極各種表現(xiàn)可能性的掙扎面貌,奧爾巴赫的線已經(jīng)融入了強(qiáng)烈的精神因素。比較而言,奧爾巴赫的線沒(méi)有德•庫(kù)寧的線抽拉般的恣意和灑脫,卻多了幾分風(fēng)骨和凌厲;沒(méi)有賈科梅蒂線的別致有序和舒展,卻更具韻致和張力;沒(méi)有馬蒂斯線的華麗、安樂(lè)以及梵高線的筆觸感,卻更具樸質(zhì)和力度。奧爾巴赫將線與形體交織在一起,又不完全從屬于形體,線條似乎隨著形體的幻影在空間交織與扭動(dòng),不斷地改變著形象,使形象彌漫出無(wú)限的意蘊(yùn),充滿著神秘和未知。
奧爾巴赫作品中線條往往給人聚散離合不定之感,這與他不懈地追求事物的內(nèi)在真實(shí)有關(guān),他不斷在形象中尋覓那種囊刮了“真實(shí)”的各個(gè)側(cè)面的形、結(jié)構(gòu)密度、重量,以及對(duì)象被消化的難易度,因而,使線的運(yùn)動(dòng)軌跡充滿著不確定性。從其作品《桑德拉肖像》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中,我們能夠清楚地感受這種面貌的形成過(guò)程,此畫結(jié)構(gòu)的每次重來(lái),用線從輕畫揉擦,幾乎渾然與邊界相融,到如鷹爪般凌厲的折線又回到幾乎空茫,如此反復(fù)過(guò)后,形象有著不同的生長(zhǎng),而每一次生長(zhǎng)痕跡又孕育了下一次的無(wú)限可能性。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線條似逐漸被賦予了更多的意涵和靈性,直至與作品的精神結(jié)合在一起。奧爾巴赫曾說(shuō)過(guò):“在一幅好畫里,每一處都是畫外更偉大的構(gòu)想所決定的,但有時(shí)這構(gòu)想直到最后才對(duì)藝術(shù)家顯現(xiàn)……。問(wèn)題在于怎樣分辨它,然后明確它。這常常令畫呼之欲出。”奧爾巴赫追求的是一種能使畫味更濃厚的用線技法,線條已經(jīng)不僅僅是線條,而是作品情緒所在、精神所在,他讓線條做到了形意并舉、形神相通,而又顯得自在和理性,達(dá)到了超凡脫俗的表現(xiàn)境界。
混沌意象的圖式空間
造型藝術(shù)的目的在于表現(xiàn)視覺(jué)形式,并將視覺(jué)形式作為特定的感覺(jué)對(duì)象呈現(xiàn)給觀眾,藝術(shù)家創(chuàng)建視覺(jué)形式會(huì)運(yùn)用各種表現(xiàn)語(yǔ)言和手段,并使這種形式富有一定的意義和意味。西方現(xiàn)代繪畫史可以說(shuō)就是形式語(yǔ)言探索與發(fā)展的歷史,奧爾巴赫的作品具有獨(dú)特的形式美感,其中一個(gè)重要方面,就是對(duì)畫面圖式空間的獨(dú)特建構(gòu)。蘇珊•朗格對(duì)空間有過(guò)精彩的論述:“繪畫的空間僅僅是一個(gè)可見(jiàn)物,對(duì)于觸覺(jué)、聽(tīng)覺(jué)和肌肉活動(dòng)是不存在的。而對(duì)于眼睛它總是充滿了各種形狀的深不可測(cè)的空間,這是一種純粹的視覺(jué)幻象空間,是一種被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空間。而這一切離開(kāi)了形狀的組織,它簡(jiǎn)直就不存在。”
事實(shí)上,正如蘇珊•朗格所說(shuō),奧爾巴赫作品的空間就是一種純粹的視覺(jué)幻象空間,而且是一個(gè)混沌意象的圖式空間。那么,這種混沌意象的圖式空間又是如何被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呢?我們知道現(xiàn)代藝術(shù)家既依據(jù)有意識(shí)的思索進(jìn)行作品創(chuàng)作,同時(shí)也依靠想象和意象,藝術(shù)家已經(jīng)從他的知覺(jué)和社會(huì)的禁錮中解脫了出來(lái),表現(xiàn)為更多的依據(jù)某種潛在意識(shí)來(lái)獲取創(chuàng)造的靈感。作為表現(xiàn)主義藝術(shù)家,奧爾巴赫不為具體形象外在因素所束縛,將線條、形塊、調(diào)子等表現(xiàn)語(yǔ)言按照自己的語(yǔ)言表達(dá)方式進(jìn)行圖式建構(gòu),從其作品的形象塑造上看,奧爾巴赫放棄了對(duì)人物外在表現(xiàn)的刻畫,弱化了人物特征對(duì)視覺(jué)的干擾,以意象的表現(xiàn)手法對(duì)形象加以處理,當(dāng)形象的諸多外在特征被抽離以后,形象的內(nèi)在性卻得到了豐富和展現(xiàn)。
在混沌意象的圖式空間中,空間已經(jīng)沒(méi)有特定的場(chǎng)所意義和時(shí)空性質(zhì),更沒(méi)有現(xiàn)實(shí)中的景深尺度,畫中的所謂空間不過(guò)是用柔性的線條涂抹揉擦而交織成的色層和痕跡,是一種具有形式意義的存在方式,而這種存在方式是為承載特定圖式物象所設(shè)定的,它的存在方式與價(jià)值取決于置身其中物象的存在方式。在奧爾巴赫的作品中往往作為背景的線條和色層、形象同構(gòu)在一起,有時(shí)根本找不到邊界,形象似乎很難從空間中分離出來(lái),形象本身就是這種圖式空間的有機(jī)體。整個(gè)畫面因此而呈現(xiàn)出特有的氣息。我們知道作品內(nèi)在氣息一般是較難體現(xiàn)的,藝術(shù)家在表現(xiàn)過(guò)程中必須努力使構(gòu)成畫面的各元素都浸在某種氣息之中,使之成為既是這種氣息的形成因子,又是這種氣息的展現(xiàn)部分。
篇3
中世紀(jì)處于古典文明的結(jié)束與復(fù)興之間,中世紀(jì)藝術(shù)屬于基督教藝術(shù),這時(shí)的藝術(shù),開(kāi)始了從“哲學(xué)情懷”到“宗教情思”的過(guò)渡的大語(yǔ)境。此時(shí)藝術(shù)變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觀世界的真實(shí)描寫,而往往以夸張、變形等手法表現(xiàn)精神世界。中世紀(jì)審美觀發(fā)生了變化,藝術(shù)品不再模仿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而是注重表現(xiàn)基督教的威嚴(yán)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體一般直立,張開(kāi)雙手,但是還是有羅馬藝術(shù)的影子。新興資產(chǎn)階級(jí)力圖復(fù)興古典文化,在造型藝術(shù)方面,以寫實(shí)傳真為首務(wù),開(kāi)創(chuàng)了基于科學(xué)理論的表現(xiàn)技法,如人體解剖和透視法等。漢魏對(duì)圖宣講的傳統(tǒng)在佛教傳播中,將佛教主題與中土的手卷畫形式有機(jī)結(jié)合;正如先秦許多繪畫是為講述而存在的,這些畫卷也是為演講者而創(chuàng)作。佛教藝術(shù)家的任務(wù)是在紙、絹上描繪佛教人物的神變,變文的講解者在講唱時(shí)即以此作為一種圖解(在這些畫卷上一般還有簡(jiǎn)要的文字提綱),按圖講說(shuō)。圖繪再次成為口頭敘事的一個(gè)重要輔助手段。
三、現(xiàn)代繪畫中與文學(xué)語(yǔ)境的同步發(fā)展
縱觀世界藝術(shù)史,文學(xué)語(yǔ)境與繪畫語(yǔ)境始終在同步發(fā)展。高明的畫家往往能夠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獨(dú)特的藝術(shù)特征和表現(xiàn)自己深刻而獨(dú)到的人生感悟。這種意境是畫家自身修為的體現(xiàn),受畫家的文學(xué)藝術(shù)修養(yǎng)的制約。文學(xué)藝術(shù)修養(yǎng)是難以琢磨的,它來(lái)源于藝術(shù)家心靈對(duì)世界和人生的獨(dú)到感受。繪畫中的文學(xué)性主要表現(xiàn)在這樣兩個(gè)方面:
篇4
(一)新繪畫的出現(xiàn)
20世紀(jì)70年新繪畫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繪畫開(kāi)始走出死胡同,有的新的發(fā)展方向,繪畫藝術(shù)開(kāi)始走出困境,走向復(fù)興。這種新的藝術(shù)形式首先在歐洲生長(zhǎng),后來(lái)美國(guó)奮起直追,到了80年代中期連日本也出現(xiàn)了這樣的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這種新繪畫的特征是風(fēng)格自由,大膽粗獷。畫面巨大,意象深遠(yuǎn),充滿了苦澀的美感。這些作品能給人強(qiáng)烈的情緒,題材也極為豐富。
(二)意象
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shù)發(fā)展到最后進(jìn)入到了死胡同,形象不存在了,色彩不存在了,空間不存在了,到后來(lái)連繪畫藝術(shù)的意義都受到質(zhì)疑。而我們的后現(xiàn)代的藝術(shù)家們另辟?gòu)袕剑瑥亩鄠€(gè)角落找回藝術(shù)的價(jià)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dāng)代的藝術(shù)家們畫面中出現(xiàn)了意象。意象是介于形象和抽象之間,這種意象既不同于傳統(tǒng)的寫實(shí)主義繪畫的惟妙惟肖的具象,也不同于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對(duì)形象的消解,它是一種抽象、殘缺不全的、怪誕離奇的、夸張的或是變形的、卡通或涂鴉形象,它以一種新方式出現(xiàn)在畫面中。新意象繪畫有許多代表畫家,其中重要人物有菲利普•古斯頓。他在1968年突然采用了一種新卡通式的具象繪畫。在新意象畫家中,最有名的當(dāng)屬蘇珊•羅森伯,她畫面中采用的具象是馬——確切的說(shuō),是用松弛的輪廓線勾勒而成的馬的側(cè)面。
三、流派紛呈,兼容并蓄
西方當(dāng)代藝術(shù)有著極強(qiáng)的包容性,它呈現(xiàn)出一個(gè)五彩繽紛的狀態(tài)。它包容一切可能的藝術(shù)形式,即使是以往難登大雅之堂的涂鴉形象。在對(duì)待藝術(shù)家這個(gè)問(wèn)題上,破除西方主流文化中心論,一些亞洲、拉美藝術(shù)家的作品也出現(xiàn)在了各地的展覽中。當(dāng)代西方繪畫藝術(shù)色彩紛呈,流派眾多。主要有聯(lián)邦德國(guó)的新表現(xiàn)主義、意大利的超前衛(wèi)藝術(shù)、美國(guó)的涂鴉藝術(shù)、法國(guó)的自由形象與英國(guó)的新精神等等。比如:
(一)德國(guó)的新表現(xiàn)主義:
德國(guó)的新表現(xiàn)主義繪畫經(jīng)歷了從巴塞利茲、呂佩爾茨的“純繪畫”到彭克、波爾克的可能性再到柏林的一些年輕的藝術(shù)家的表現(xiàn)力的繪畫,使得繪畫獲得了新生。這一派的藝術(shù)家試圖消解繪畫的主題和內(nèi)容,用富有張的藝術(shù)形象來(lái)吸引關(guān)注。這一派的藝術(shù)家們認(rèn)為繪畫應(yīng)該是自由的,無(wú)限制的。比如畫家基弗就收集了從神話到近現(xiàn)代的所有史料,用繪畫的方式把這種歷史表現(xiàn)了出來(lái)。他們還用強(qiáng)烈的色彩,大膽的畫風(fēng)表現(xiàn)內(nèi)心被壓抑的情緒。
(二)意大利的前衛(wèi)藝術(shù)家:
在意大利超前衛(wèi)的藝術(shù)家那里就采用了折衷風(fēng)格,他們借鑒了傳統(tǒng)繪畫的風(fēng)格和規(guī)則。在其代表人物基亞那里可以看到夏加爾、畢加索等藝術(shù)家的影子,但基亞不是照抄或延續(xù)這種風(fēng)格,也是進(jìn)行新的詮釋和演繹,使古典以新的面目進(jìn)行回歸。而庫(kù)奇尤其喜歡馬薩喬的藝術(shù),他繼續(xù)探討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在這里,藝術(shù)家們不是把這些風(fēng)格簡(jiǎn)單排列,而是進(jìn)行多方面的組合和探索,使一些新的表現(xiàn)成為可能。
(三)美國(guó)的涂鴉藝術(shù):
它的代表人物有吉斯哈•林、肯尼•莎爾夫等。吉斯•哈林的藝術(shù)有一種華麗之感,幽默、活潑,他的粉筆畫也迅速、簡(jiǎn)潔。而另一個(gè)代表人物肯尼•莎爾夫是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涂鴉藝術(shù)家,他的畫面色彩明亮,有一種極端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刺激效果。
(四)法國(guó)的自由形象:
這一派的藝術(shù)家作品中形象具有濃厚的諷刺意味。他們或取材于海報(bào),或取材于卡通人物,有著一定的喜劇效果。英國(guó)的新精神:這一派的代表畫家馬爾科姆•莫利談?wù)撍囆g(shù)家通過(guò)藝術(shù)了解潛意識(shí),通過(guò)意象讓潛意識(shí)活動(dòng)暴露出來(lái)。他們或在叛逆者中尋找繪畫形象,或在詩(shī)人中尋找。這是一種有較大隨意性的創(chuàng)作方法。
篇5
素描、色彩,是所有學(xué)習(xí)美術(shù)專業(yè)學(xué)生必修的基礎(chǔ)繪畫課程,在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學(xué)體系中,把它們作為基礎(chǔ)繪畫教育課程,有我國(guó)多年藝術(shù)教育的歷史原因。長(zhǎng)期以來(lái),素描、色彩課程一直被認(rèn)為是一切造型藝術(shù)的基礎(chǔ),但在學(xué)習(xí)設(shè)計(jì)的過(guò)程中,大多數(shù)學(xué)生很難把基礎(chǔ)繪畫課和設(shè)計(jì)專業(yè)結(jié)合在一起,只注重繪畫寫生和技法的訓(xùn)練,而忽視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專業(yè)性,牽制了學(xué)生設(shè)計(jì)思維的發(fā)展。在過(guò)去,我們的藝術(shù)教育強(qiáng)調(diào)基礎(chǔ),強(qiáng)調(diào)繪畫功底,在這種情形下著實(shí)培養(yǎng)了一批批寫實(shí)功夫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過(guò)硬的畫家,以至于這些畫家至今還陶醉于花費(fèi)數(shù)月表現(xiàn)一個(gè)比真的還真實(shí)的手工繪畫作品的滿足感受中。現(xiàn)在的書店里,我們會(huì)經(jīng)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書籍被命名為“正規(guī)畫法、正規(guī)范畫”的字語(yǔ),難道除了他們的畫法外,其他人的繪畫風(fēng)格都是旁門左道嗎?何謂“正規(guī)”,藝無(wú)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風(fēng)格,即是走到了終點(diǎn),接下來(lái)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這樣藝術(shù)才能進(jìn)步,我們才能創(chuàng)新。如今是一個(gè)數(shù)字技術(shù)、多媒體影像可以輕松去復(fù)制作品,可設(shè)計(jì)藝術(shù)卻不能去重復(fù)、去拷貝,因?yàn)樵O(shè)計(jì)追求的是原創(chuàng)性和創(chuàng)新性;目前我們的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原創(chuàng)設(shè)計(jì)和國(guó)際上一些優(yōu)秀的設(shè)計(jì)相比顯得有些滯后,看看近年來(lái)一些產(chǎn)品造型專業(yè)的萎縮狀況,一些大型的優(yōu)秀建筑環(huán)境藝術(shù)設(shè)計(jì)、服裝設(shè)計(jì)都來(lái)自于國(guó)外的設(shè)計(jì)師即可而知。我們的一些設(shè)計(jì)師的創(chuàng)造力相對(duì)就顯得有些蒼白,這是不是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基礎(chǔ)忽視創(chuàng)造力培養(yǎng)的結(jié)果,是不是所謂“正規(guī)”的繪畫基礎(chǔ)教育造成的?這就需要每個(gè)從事設(shè)計(jì)藝術(shù)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們的“繪畫基礎(chǔ)”和功底的了。
篇6
2.繪畫具有具象性,人與生命是創(chuàng)作的永恒主題
桑德羅•基亞的繪畫是具象的,而且他的創(chuàng)作主題始終沒(méi)有離開(kāi)人與生命。他的繪畫充滿神話和隱喻的色彩,但不具備情節(jié)性。他將古典的題材和隨意的畫法結(jié)合在一起,作品形象具有顯著的體積感,多種曲直線的運(yùn)用又使畫作具有抽象和具象結(jié)合的因素。《背水產(chǎn)者》中碩大的魚的形象得自古希臘神話中的動(dòng)物形象,背水產(chǎn)的男人形象則來(lái)源于古希臘雕塑,這種具象的物象輔以背景的深紅色地面和藍(lán)白色海水,以及人物右側(cè)的曲線團(tuán)塊的對(duì)比,使畫面形式感具有一種別樣的意味。
3.繪畫形象具有多重意義
桑德羅•基亞有著良好的色彩感,畫面不但令人賞心悅目,同時(shí)極具戲劇性與幽默感,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還配有一段作品的解說(shuō)詞或小詩(shī)。桑德羅•基亞用靈敏的藝術(shù)感覺(jué)與時(shí)刻流動(dòng)著的藝術(shù)意識(shí),將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史變成了一幅多種風(fēng)格并存的畫面。對(duì)于桑德羅•基亞來(lái)說(shuō),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個(gè)小的中轉(zhuǎn)站,他通過(guò)創(chuàng)作不同的作品,并讓這些作品彼此達(dá)到最大限度的融合,最終構(gòu)成其獨(dú)特的個(gè)人風(fēng)格。
篇7
動(dòng)畫誕生于繪畫,利用人類的視覺(jué)暫留理論,將24格連續(xù)畫面形成一秒鐘流動(dòng)的影像。所以每一秒鐘的每一幀畫面都充分體現(xiàn)著動(dòng)畫導(dǎo)演的個(gè)人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和畫風(fēng)。色彩、線條、光影等這些構(gòu)圖元素同樣是動(dòng)畫風(fēng)格的表現(xiàn)元素。動(dòng)畫導(dǎo)演通過(guò)不同的筆觸、節(jié)奏、線條、光影讓“畫”“動(dòng)”起來(lái),所以不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導(dǎo)演就可以利用不同線條和色塊體現(xiàn)自己的動(dòng)畫風(fēng)格和藝術(shù)審美。宮崎駿的吉卜力工作室有數(shù)百名手繪工作者,不同的人負(fù)責(zé)不同的畫面構(gòu)圖,比如全景的山川森林、近景或特寫的物體等,而電影的核心人物形象塑造由宮崎駿掌控創(chuàng)作的指導(dǎo),所以在宮崎駿的動(dòng)畫里體現(xiàn)了線條、色塊的多元化。加拿大女導(dǎo)演特里爾•科夫擅長(zhǎng)利用簡(jiǎn)單的線條營(yíng)造輕信質(zhì)樸的畫面風(fēng)格,具有蒙德里安的幾何抽象的繪畫風(fēng)格,其代表作《丹麥詩(shī)人》在創(chuàng)作中先用鉛筆進(jìn)行線條勾勒,之后用油彩著色,畫面虛實(shí)結(jié)合、明暗分明。法國(guó)Cube動(dòng)畫工作室擅長(zhǎng)利用線條形成動(dòng)畫的運(yùn)動(dòng)方向和節(jié)奏,在喜劇動(dòng)畫中給人流暢自然的審美感官,代表作是《愛(ài)情是什么》。
三、寫實(shí)與寫意相結(jié)合的獨(dú)特審美意境
我國(guó)的傳統(tǒng)繪畫以水墨畫的寫意為主,具有東方的感性特征。而西方繪畫藝術(shù)以寫實(shí)為主,體現(xiàn)在繪畫的透視和色彩的逼真上。這些繪畫的特征也表現(xiàn)在了東西方手繪動(dòng)畫的審美意境上。我國(guó)早期的手繪動(dòng)畫片,比如《小蝌蚪找媽媽》、《牧笛》、《大鬧天宮》等都具有寫意風(fēng)格;而美國(guó)的迪士尼動(dòng)畫就以視覺(jué)效果的逼真性為追求,采用真人表演動(dòng)畫然后進(jìn)行手繪創(chuàng)作畫面,結(jié)合繪畫中的透視、光影和人體構(gòu)造學(xué)等。在動(dòng)畫創(chuàng)作中極大增強(qiáng)了畫面的真實(shí)感,視覺(jué)效果強(qiáng)烈,震撼觀眾。美國(guó)動(dòng)畫產(chǎn)業(yè)占據(jù)了世界動(dòng)畫片出口的80%以上,具有不可抗拒的地位,其動(dòng)畫片創(chuàng)作均采用寫實(shí)風(fēng)格,利用手繪創(chuàng)作與現(xiàn)代的計(jì)算機(jī)CG技術(shù)相結(jié)合,并通過(guò)真人模擬演繹進(jìn)行計(jì)算機(jī)畫面生成。
篇8
二、中西方繪畫藝術(shù)形態(tài)的差異
篇9
中國(guó)的深化改革伴隨著世界一體化進(jìn)程的影響,我們的設(shè)計(jì)也出現(xiàn)在一個(gè)新的模式。設(shè)計(jì)概念是逐步縮小與國(guó)際的距離。說(shuō)明當(dāng)代的設(shè)計(jì)趨勢(shì)就是好的設(shè)計(jì)不僅具有科學(xué)技術(shù)的先進(jìn)水平,而且更要具有獨(dú)特的文化哲學(xué)。我們普遍的認(rèn)為國(guó)家以及民族靈魂是由文化體現(xiàn)的,而文化差異是各個(gè)國(guó)家的根本區(qū)別。民族中的傳統(tǒng)文化被認(rèn)為是這個(gè)民族的根基,民族性就是體現(xiàn)在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全球文化交流。繪畫意境中的民族傳統(tǒng)藝術(shù)可以將人與自然融為一體。我們的畫家在繪畫創(chuàng)作中追求的繪畫語(yǔ)言不再是展現(xiàn)純目的不是純主觀抽象的追求。我國(guó)傳統(tǒng)繪畫的永恒的創(chuàng)作原則是“中心得源、外師造化”。大多數(shù)的中國(guó)歷代畫家常以自然界中的借景抒情為主題來(lái)寬慰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挫折,這是中國(guó)獨(dú)有的逃避現(xiàn)實(shí)的方式。在繪畫的過(guò)程中畫家的情緒也得到了釋懷,散發(fā)出水墨寫意的精神,巧妙地將主觀與客觀的理解融為一體,利用象征手法將自然對(duì)象與個(gè)人情感結(jié)合。將這種方式利用到現(xiàn)在的藝術(shù)教育當(dāng)中,將傳統(tǒng)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育的靈魂進(jìn)行傳承可以拓寬學(xué)生的思維,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線條與水墨能夠使中國(guó)畫的表現(xiàn)元素更加豐富,所以我國(guó)的繪畫著重強(qiáng)調(diào)其重要性,線的曲直方圓,排列的緊迫性、剛?cè)岬淖兓龋伎梢赃_(dá)到自己情緒的表現(xiàn)和抒情的目的,使用不同的線給人不同的個(gè)性特征和情緒的表達(dá)。為了了解中國(guó)繪畫中線的豐富的審美意蘊(yùn),必須掌握水墨的規(guī)律和方法,使我們能深刻理解內(nèi)涵的中國(guó)繪畫和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繪畫語(yǔ)言的設(shè)計(jì)可以實(shí)現(xiàn)深遠(yuǎn)的視覺(jué)效果,能提高豐富的藝術(shù)內(nèi)涵。“隨類賦彩”這種技法是中國(guó)畫的重要技法,心理學(xué)上認(rèn)為的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性格在我國(guó)的繪畫中早有體現(xiàn)。豐富的色彩通過(guò)勾金和重彩等技法表現(xiàn),具有裝飾特點(diǎn)。水墨的濃淡表現(xiàn)不同色彩是微妙的地方,顏色是簡(jiǎn)單而精致的。皴法不僅是凹凸表面紋理繪畫表現(xiàn),更形象的認(rèn)識(shí)和再創(chuàng)造的“體面”和“肌理”。傳承中國(guó)畫的這些技術(shù)可以成為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育中傳統(tǒng)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為進(jìn)一步提高學(xué)生的文化藝術(shù)修養(yǎng)創(chuàng)造基礎(chǔ)。日本是世界著名的設(shè)計(jì)之邦,其傳統(tǒng)審美將他們的設(shè)計(jì)教育與民族文化傳承的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借鑒他們的成功經(jīng)驗(yàn):便是傳統(tǒng)文化對(duì)現(xiàn)代設(shè)計(jì)的意義有深遠(yuǎn)的影響。部分人看來(lái),這個(gè)時(shí)代的矛盾看似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duì)立。實(shí)際是他們的完全融合,相互滲透。要發(fā)揚(yáng)傳統(tǒng),只有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現(xiàn)代設(shè)計(jì)中從傳統(tǒng)文化的本質(zhì)內(nèi)涵提煉與學(xué)習(xí),使其具有鮮明的民族風(fēng)格和較高的使設(shè)計(jì)的審美價(jià)值。
三、學(xué)生的藝術(shù)素養(yǎng)相對(duì)的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
當(dāng)代教育認(rèn)為藝術(shù)素養(yǎng)是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的基本思想,它決定了設(shè)計(jì)思想和設(shè)計(jì)語(yǔ)言的廣度深度。成功者的經(jīng)驗(yàn)告訴我們良好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可以體現(xiàn)設(shè)計(jì)師的質(zhì)量,它更是不容易獲得的,需要長(zhǎng)期的專業(yè)訓(xùn)練和對(duì)藝術(shù)的欣賞才可慢慢培養(yǎng)起來(lái)。自身的水平得到提高后,再不斷的增加藝術(shù)知識(shí)的儲(chǔ)備。這樣一來(lái)對(duì)于藝術(shù)教育中學(xué)生的設(shè)計(jì)能力的欠缺就會(huì)有一定的補(bǔ)償作用,加上不斷地藝術(shù)基本功訓(xùn)練通過(guò)創(chuàng)意的結(jié)合便能設(shè)計(jì)出具有審美創(chuàng)造力的設(shè)計(jì)。跨專業(yè)的知識(shí)點(diǎn)也可以在設(shè)計(jì)中充分體現(xiàn),設(shè)計(jì)才能不斷地推陳出新。而學(xué)有所成的設(shè)計(jì)師的文化內(nèi)涵和藝術(shù)修養(yǎng)都能通過(guò)他們的作品得出結(jié)論,這些歷經(jīng)現(xiàn)代設(shè)計(jì)市場(chǎng)考研的經(jīng)驗(yàn)對(duì)藝術(shù)設(shè)計(jì)學(xué)習(xí)中國(guó)畫教育是提高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培養(yǎng)至關(guān)重要。
四、中國(guó)畫教學(xué)在藝術(shù)設(shè)計(jì)中的引用
由于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已經(jīng)知道現(xiàn)代中國(guó)畫的概念,那么中國(guó)將如何借鑒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學(xué)也很值得討論。藝術(shù)與設(shè)計(jì)的中國(guó)畫教學(xué),不僅僅是文字,學(xué)習(xí)和培訓(xùn)的技能,在中國(guó)畫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育應(yīng)該有其特殊性不同于純繪畫類中國(guó)畫教育,應(yīng)根據(jù)培養(yǎng)目標(biāo),教學(xué)計(jì)劃,共同設(shè)計(jì)和繪畫中找到。畫中國(guó)畫課程只注重技能的訓(xùn)練,并在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育與設(shè)計(jì)相關(guān)的中國(guó)畫教學(xué)。筆者認(rèn)為,在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育中國(guó)畫教學(xué),主要從三個(gè)方面:
1.中國(guó)繪畫與設(shè)計(jì)一體化的形式
中國(guó)畫的形式和技術(shù)的教學(xué)內(nèi)容是必要的。這部分主要是關(guān)于中國(guó)畫的筆墨語(yǔ)言和風(fēng)格教學(xué)。例如:在作文課上,文本元素如點(diǎn),線,面。廣告海報(bào),我們有意識(shí)地選擇一些中國(guó)畫的元素進(jìn)行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的學(xué)生標(biāo)志設(shè)計(jì)。
2.現(xiàn)代精神追求中的中國(guó)繪畫和現(xiàn)代設(shè)計(jì)
中國(guó)繪畫經(jīng)常研究的是意象和表象的意義,類似于書寫形式。中國(guó)畫的主要思想包含的繪畫活動(dòng)的感受,人與自然之間,但天生的性格,也自然人格。因此在第二自然美的藝術(shù)美——人與自然。當(dāng)今世界是和諧理念的追求,在人與自然的推廣,這也與中國(guó)畫的精神遙相呼應(yīng),同時(shí)還設(shè)計(jì)了圍繞這一思路,并以此為主導(dǎo)。藝術(shù)設(shè)計(jì)專業(yè)教育中國(guó)畫教學(xué)使學(xué)生了解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內(nèi)涵是中國(guó),并融入現(xiàn)代設(shè)計(jì)理念,成為我們自己的民族藝術(shù)風(fēng)格。
3.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培養(yǎng)
必須在藝術(shù)設(shè)計(jì)教學(xué)中創(chuàng)造性思維訓(xùn)練到底在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進(jìn)一步提高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不斷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新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中國(guó)畫的水墨語(yǔ)言和洗千變?nèi)f化,中國(guó)畫更耐人尋味,這本身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體現(xiàn)活動(dòng)。中國(guó)畫教學(xué),我們要求學(xué)生充分利用藝術(shù)形式,不同的紋理,使畫面更具設(shè)計(jì)感。設(shè)計(jì)本身是由西方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活動(dòng)的原則,中國(guó)畫獨(dú)特的形式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語(yǔ)言符號(hào),中西元素結(jié)合在一起,是設(shè)計(jì)形式的創(chuàng)新。中國(guó)畫與設(shè)計(jì)可以作為一個(gè)起點(diǎn),從新的角度,全面發(fā)展相結(jié)合的中國(guó)畫和藝術(shù)設(shè)計(jì)學(xué)生潛在的藝術(shù)和審美人格,有利于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培養(yǎng)。
篇10
一、抽象性繪畫中的藝術(shù)形態(tài)
西方人自古以來(lái)就對(duì)和諧、勻稱、均衡等形式法則有著特殊的興趣,很多西方藝術(shù)家在造型應(yīng)用中自覺(jué)地去尋找其中的規(guī)律與法則,并將他們尋找出來(lái)的結(jié)果不斷發(fā)揚(yáng)、傳播,引導(dǎo)一批又一批的藝術(shù)家追隨他們探索出的腳印繼續(xù)前行。尤其是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很多畫家都以科學(xué)的手段探索美的形式。他們想通過(guò)數(shù)學(xué)的形式找到美的規(guī)律,以至于花費(fèi)大量的時(shí)間來(lái)研究透視、解剖,并且用數(shù)字比例的方式將其記錄下來(lái),以便于使美的形式與法則得以延續(xù),當(dāng)然這只是一種理想的愿望而已,從很多古典大師所畫的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些。直到經(jīng)歷過(guò)巴洛克、洛可可、浪漫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新古典主義等直到印象主義,一些畫家才開(kāi)始強(qiáng)調(diào)并實(shí)踐于用色彩來(lái)表達(dá)主觀思想和情感,他們強(qiáng)調(diào)另外的繪畫方式:繪畫中色彩的抽象和幾何的抽象。縱觀西方繪畫,可以看出,注重形式表達(dá)的繪畫和注重色彩感情的繪畫是其基本的藝術(shù)形態(tài),而抽象繪畫則是在二者之中發(fā)展而來(lái)。隨著繪畫的發(fā)展人們不再屈從于學(xué)院派的主導(dǎo)思想,嚴(yán)格地忠實(shí)于客觀現(xiàn)實(shí)存在而反復(fù)訓(xùn)練,而是相應(yīng)地發(fā)展了現(xiàn)代主義繪畫中抽象性繪畫的各個(gè)流派,直到后現(xiàn)代主義各個(gè)畫派。
二、抽象性繪畫賞析概要
我們一般所說(shuō)的“抽象藝術(shù)”是指沒(méi)有具體形象的,或者說(shuō)非再現(xiàn)性的藝術(shù),藝術(shù)中的抽象不同于自然科學(xué)中的抽象,藝術(shù)中的抽象具有獨(dú)特的不可言說(shuō)性。美術(shù)史中所說(shuō)的抽象主義主要是由康定斯基為代表的熱抽象和以蒙德里安為代表的冷抽象。這些作品進(jìn)入了一個(gè)更高的精神層次,往往表達(dá)的是一種藝術(shù)觀念,畫面中放棄了具體的內(nèi)容和情節(jié),突出運(yùn)用點(diǎn)、線、面、色塊、構(gòu)圖等純粹的繪畫語(yǔ)言表現(xiàn)內(nèi)心的感覺(jué)、情緒、節(jié)奏等抽象的內(nèi)容。抽象油畫通常以直覺(jué)和想象力為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diǎn)。比如,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的作品,就帶有一些神秘主義者的思想,想讓他們的藝術(shù)區(qū)域揭示在主觀性的外形不斷變化的背后隱藏著的永恒不變的實(shí)在,所以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排斥任何具有象征性、文學(xué)性、說(shuō)明性的表現(xiàn)手法,這樣就很難使人理解,抽象油畫作品僅將造型和色彩加以綜合、組織,完全顛覆了傳統(tǒng)審美觀念。理想之美、自然之美是抽象繪畫極力要擺脫、避免的東西。抽象繪畫的基本特征是取消了對(duì)物象具體描繪,而改用情緒的方法去表現(xiàn)概念和作畫,因此這種方法也可以說(shuō)是表現(xiàn)主義的。它是由各種反傳統(tǒng)的藝術(shù)融合而來(lái),特別是由野獸派、立體派演變而來(lái)。無(wú)論是再現(xiàn)還是表現(xiàn),繪畫都是通過(guò)形與色來(lái)實(shí)現(xiàn)自身存在意義的,如果抽象繪畫藝術(shù)的解讀成了一個(gè)難題,沒(méi)有人能夠看懂,那它依然會(huì)失去存在的價(jià)值。在米歇爾•塞弗爾看來(lái),抽象藝術(shù)是:“我把一切不帶任何提醒,不帶任何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回憶,不管這一現(xiàn)實(shí)是否是畫家的出發(fā)點(diǎn)的藝術(shù),都叫作抽象藝術(shù)。”但無(wú)論是立體主義創(chuàng)始人畢加索,還是野獸派代表馬蒂斯等人的作品,它們的共同點(diǎn)都是極大地貶低了畫面的具象寫實(shí)性。當(dāng)然比起以康定斯基為代表的熱抽象與以蒙德里安為代表的冷抽象,畢加索追求的立體主義與馬蒂斯所表現(xiàn)強(qiáng)烈色彩的野獸派還沒(méi)有取消具象結(jié)構(gòu)與內(nèi)在意義。康定斯基要求取消物體而表達(dá)內(nèi)在意義,他從音樂(lè)的啟示中提出這種理想,在1910年繪出《抽象水彩》,由于多種原因,隨后他也有過(guò)多樣性的探索,而在晚年達(dá)到了幾近神秘主義的境界。蒙德里安從建筑中得到啟示,而通過(guò)立體主義發(fā)展了幾何構(gòu)圖的傾向。他對(duì)樹這一主題進(jìn)行不斷抽象化的組畫《樹》風(fēng)靡一時(shí),后來(lái)集中于新造型藝術(shù)的探索,這種新藝術(shù)在構(gòu)圖上只使用橫直位置上的直角,在色彩上只使用三原色和黑白灰進(jìn)行作畫。這種構(gòu)型具有獨(dú)特的美學(xué)效果,但是畫家賦予的意義卻不具有解釋性。在對(duì)抽象繪畫有了整體的認(rèn)識(shí)之后,我們面對(duì)看不懂的作品時(shí)可以停下腳步通過(guò)畫面色彩的運(yùn)用與形式的組織,結(jié)合我們平時(shí)積累的知識(shí)來(lái)玩味抽象藝術(shù)的美妙。當(dāng)我們的心靈與呈現(xiàn)在眼前的作品產(chǎn)生共鳴時(shí),會(huì)發(fā)現(xiàn)原來(lái)繪畫也可以如此表現(xiàn)。
作者:趙文博 單位:天水師范學(xué)院
篇11
審美中出現(xiàn)了丑。“丑”出現(xiàn)在繪畫藝術(shù)中是起源于法國(guó)的象征主義。藝術(shù)家接二連三地高聲呼喊,把丑送上了繪畫藝術(shù)的歷史舞臺(tái),并且這一觀點(diǎn)廣泛地影響到很多國(guó)家,在文學(xué)和藝術(shù)領(lǐng)域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藝術(shù)生活中開(kāi)始出現(xiàn)了丑惡美。在古代繪畫藝術(shù)中,是種和諧的美,是對(duì)美的模擬和仿照。正如周來(lái)祥先生概括的“古代樸素的和諧美”,古典繪畫藝術(shù)的審美特征是努力表現(xiàn)藝術(shù)中的魅力,再現(xiàn)生活中的美景。現(xiàn)當(dāng)代繪畫中“丑”的審美形象如蒙克的繪畫作品《吶喊》,在這一作品中展現(xiàn)了一個(gè)骷髏,骷髏在痛苦地掙扎著,充滿了恐懼。作品中描繪的不僅僅是表面的丑陋,同時(shí)反映出的是社會(huì)的病態(tài)和人性的丑惡,這種直觀的表達(dá)與那種朦朧的詩(shī)意是截然不同的。當(dāng)代繪畫藝術(shù)抽離了作品中的畫面意義。在繪畫藝術(shù)發(fā)展到當(dāng)代,繪畫者對(duì)形式的重視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了以前,尤其是印象派的畫家們,他們最為強(qiáng)調(diào)直觀的感受,繪畫的是畫者瞬間的感受,對(duì)于畫面的內(nèi)容不是很重視。而立體派完全顛覆了以前的形式,把正常的形象肢解,然后肆意地重組,根本就談不上作品畫面的意義。在現(xiàn)當(dāng)代繪畫作品中,看到的是作品帶給觀者的速度美和視覺(jué)沖擊力,與古典繪畫作品中的寧?kù)o和和諧是不一樣的。現(xiàn)在的繪畫藝術(shù)重視色彩、形狀和作品的材質(zhì)對(duì)觀者的影響,作品的內(nèi)容和畫面的意義被剝離開(kāi)來(lái),沒(méi)有了內(nèi)容的意義,形式變得理性化,觀者對(duì)作品的辨識(shí)也變得模糊,使觀者的情感受到一定的影響。藝術(shù)理解的私有化。只注重藝術(shù)家私人的思想意識(shí),缺少一定的內(nèi)涵。在作品中很難看到深度的影子,沒(méi)有了歷史和對(duì)未來(lái)的憧憬,同時(shí)這也是現(xiàn)當(dāng)代繪畫藝術(shù)詩(shī)性喪失的原因之一。在作品中,觀者感受不到這特有的私人情緒,覺(jué)得畫家的個(gè)人情感過(guò)于主觀,不能與觀者形成共鳴,影響思想情感的溝通。像《風(fēng)中的新娘》,由于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個(gè)人元素,觀者很難真正地了解畫家的意圖,看到的只是精神的焦慮和神情的痛苦。這種諷刺直接明了地呈現(xiàn)在了觀者的面前,會(huì)對(duì)觀者形成較大的震撼,但是沒(méi)有了蘊(yùn)涵的內(nèi)容,缺少了更深層次的意義。
三、當(dāng)代繪畫藝術(shù)詩(shī)性的缺失
當(dāng)代繪畫藝術(shù)沒(méi)有了那種徜徉在林中,讓人生發(fā)出無(wú)限的回味和遐想的意境,嗅不到古典繪畫藝術(shù)中熟悉的味道,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的畫面變成了一次次視覺(jué)的沖擊和心靈的震顫,這驚愕之情在當(dāng)代繪畫藝術(shù)作品面前顯得竟是合情合理、恰如其分。小便器作為生活用品出現(xiàn)在我們周圍,不論怎樣,對(duì)我們的震顫應(yīng)該不會(huì)多么強(qiáng)烈,即使有著開(kāi)玩笑的色彩。但當(dāng)杜尚將其搬到展覽館時(shí),卻引發(fā)了現(xiàn)當(dāng)代繪畫藝術(shù)界的轟動(dòng),杜尚僅僅將小便器改名為“泉”,這就使生活用品變成了藝術(shù)品。或許我們周圍的一切都是上天眼中的藝術(shù)品,只是我們被匆忙的社會(huì)沖昏了頭腦,沒(méi)有時(shí)間去欣賞,久而久之,也就被忽略掉了。從某個(gè)角度來(lái)說(shuō),現(xiàn)當(dāng)代的繪畫藝術(shù)可以總結(jié)為機(jī)械地復(fù)制時(shí)代,也就是對(duì)周圍事物的盲目復(fù)制和挪用,沒(méi)有了自己主觀的思維與情緒的融入。藝術(shù)真正的氣質(zhì)———韻味在現(xiàn)當(dāng)代的繪畫藝術(shù)中已經(jīng)不多見(jiàn)了,甚至有消失殆盡之意。繪畫作品中的韻味使作品瞬間有了靈性,就像一座曠古的高山,經(jīng)過(guò)雨水的洗禮,一道道瀑布從懸崖傾瀉而下,在這一刻,山中所有的寂寥和空虛頓時(shí)成為詩(shī)意。猶如中國(guó)古典繪畫藝術(shù)中的繪畫意境,幾種簡(jiǎn)單的意象經(jīng)過(guò)畫者簡(jiǎn)單的羅列和修飾,就會(huì)在無(wú)形中生發(fā)出來(lái)畫中沒(méi)有的東西,雖說(shuō)在畫中沒(méi)有實(shí)物的展示,但觀者真真切切地感覺(jué)到了它的存在,并且是清晰的,帶有自己感情的東西,這就是意境,也就是繪畫作品中的韻味,這種韻味就是“象外之象”的繪畫意境,這意境會(huì)使觀者遐思,產(chǎn)生自己的審美感受。
就像中國(guó)的古詩(shī),簡(jiǎn)單的幾個(gè)文字經(jīng)過(guò)韻律的編排就會(huì)產(chǎn)生無(wú)窮的魅力,達(dá)到用有限的文字描寫豐富的感情的效果,即使傳達(dá)的感情帶有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但是這感情是由作者所激發(fā)的。如元代馬致遠(yuǎn)的小令《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fēng)瘦馬。夕陽(yáng)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首簡(jiǎn)單的曲子是由多種常見(jiàn)的秋天景物組成,幾種景物組合成了一幅凄涼的秋天郊外的夕照?qǐng)D。浪跡天涯的游子,牽著一匹馬兒,由于長(zhǎng)途奔波、勞累,馬顯得消瘦、疲倦。夕陽(yáng)中的古道旁,有一條淺淺的小河,河水清澈卻有些凜冽,橫跨河流的小橋在秋風(fēng)中瑟縮著,飄滿了落葉。橋的盡頭一棵近乎干枯的老柳樹矗立著,猶如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老者,附近的藤蔓依舊緊緊地纏繞著自己,雖然已經(jīng)干枯,但是依然可見(jiàn)盛夏時(shí)的妖嬈。這就是古典繪畫藝術(shù)中的詩(shī)性,《天凈沙•秋思》屬于詩(shī)中的畫,用極其簡(jiǎn)單的言語(yǔ)表達(dá)出了豐富的內(nèi)涵,極為凝練的語(yǔ)言下卻包含了巨大的容量,并且意蘊(yùn)深遠(yuǎn),把飄零天涯浪子的思鄉(xiāng)情刻畫得淋漓盡致。這就是詩(shī)中意境的作用,可以生發(fā)出巨大的力量,使情境變得鮮活,并且能夠無(wú)止境地拓展。繪畫中也具備這種意境,繪畫的線條、色彩通過(guò)這些構(gòu)圖的安排,就可以在觀者面前呈現(xiàn)富有動(dòng)態(tài)、節(jié)奏的畫面,或者是由描繪出來(lái)的景物聯(lián)想到?jīng)]有的景物。在《林泉高致•畫意》中郭熙說(shuō):“詩(shī)是無(wú)形畫,畫是有形詩(shī)。”這就是繪畫的詩(shī)性,在繪畫中能夠表達(dá)出畫者特定的情感和思想,并且可以達(dá)到一語(yǔ)生萬(wàn)情的效果。“詩(shī)要求畫,以自然物狀之和諧納于文字聲律;畫亦要求詩(shī),以宇宙生生之節(jié)奏,人間心靈之呼吸和血脈之流動(dòng),托于線條色彩。”繪畫有了詩(shī)意,也就具備了繪畫的韻味,讓人產(chǎn)生審美情趣。繪畫藝術(shù)的詩(shī)性是由觀者產(chǎn)生的,對(duì)作品的感受,這種感受是由畫者的繪畫藝術(shù)刺激產(chǎn)生的,觀者觀看產(chǎn)生直觀的情感召喚,并且樂(lè)于觀賞。繪畫作品對(duì)于觀賞者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刺激源,繪畫中的詩(shī)性是作品的內(nèi)容的體現(xiàn),好的作品,可以通過(guò)分析作品來(lái)汲取藝術(shù)詩(shī)性的特質(zhì)。繪畫藝術(shù)發(fā)展到目前,尤其是當(dāng)代繪畫藝術(shù),客觀外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審美性質(zhì)也有了質(zhì)的改變。
篇12
莫高窟壁畫為了傳達(dá)宗教情緒,不斷創(chuàng)造出新的壁畫內(nèi)容,這不僅豐富了壁畫的表現(xiàn)形式,也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構(gòu)圖形式。莫高窟壁畫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往往決定了其構(gòu)圖方式,根據(jù)不同內(nèi)容會(huì)呈現(xiàn)不同構(gòu)圖。如對(duì)稱式構(gòu)圖大多是以經(jīng)變畫為主要表現(xiàn)題材,以中軸線為中心的對(duì)稱構(gòu)圖,中軸線兩側(cè)人物和場(chǎng)景都相同或相似,形成有規(guī)律的排列方式;長(zhǎng)卷式構(gòu)圖則重在描繪隋代、唐代故事畫及盛大的宗教或出行禮儀場(chǎng)面;并列式構(gòu)圖在敦煌石窟壁畫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體現(xiàn)在石窟千佛洞中的千佛圖案上,佛像大小、形態(tài)、動(dòng)作基本相同,橫成行,豎成列成并排式排列。敦煌莫高窟壁畫的結(jié)構(gòu)布局依照一定的形式法則來(lái)繪制,如此多樣化的構(gòu)圖,不僅富有強(qiáng)烈的裝飾效果,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佛教藝術(shù)的意境美。永樂(lè)宮三清殿壁畫構(gòu)圖宏偉壯麗、氣象莊嚴(yán),屬于滿構(gòu)圖類型。人物并肩接踵,按對(duì)稱儀仗形式進(jìn)行排列組合,八位主神高達(dá)近3米,在畫面突出而醒目的位置,其余270多尊神祇都在2米以上,均被整齊劃一地安排在一個(gè)氣勢(shì)磅礴的畫面中,眾仙們手持的各種道具使畫面人物靈活多變,頭頂部的祥云和腳下的云氣煙霧拓展了畫面空間,讓人仿佛置身于道教仙界的圣境之中。整幅畫面構(gòu)圖飽滿,嚴(yán)整而生動(dòng),群像組合動(dòng)靜相參、疏密有致。可見(jiàn)在永樂(lè)宮壁畫中,畫家既采用了疏密相間、統(tǒng)一中求變化,又采取突出主體,弱化次要部分的構(gòu)圖法則,具有一種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沖擊力,使人產(chǎn)生敬畏之心和崇拜之情,從而體現(xiàn)了畫家高超、純熟的構(gòu)圖技巧。伊斯蘭教繪畫藝術(shù)中的構(gòu)圖法則堅(jiān)持伊斯蘭教的基本原則。清真寺建筑裝飾構(gòu)圖的特點(diǎn)是繁復(fù)致密,幾乎不留空白,這與漢族傳統(tǒng)建筑裝飾紋樣在布局上喜歡運(yùn)用疏密相間的法則大不相同。因?yàn)橐了固m教認(rèn)為,構(gòu)圖中是不能有空間的,空間是魔鬼出沒(méi)的地方,世間的空白并不存在,而真主卻無(wú)時(shí)無(wú)處不在。所以伊斯蘭教的畫師們?cè)跇?gòu)圖形式上采用繁雜的裝飾紋樣來(lái)反映伊斯蘭建筑藝術(shù)崇尚繁瑣、不喜空白的審美特征。如寧夏中華回鄉(xiāng)文化園,其門樓頂部的幾何裝飾紋樣,以密集性、連續(xù)性的花紋組成整體的圖案,通過(guò)經(jīng)緯線、對(duì)角線的巧妙應(yīng)用,利用格子式、回環(huán)式等構(gòu)圖的交叉重組、循環(huán)變換,形成了繁密華麗的視覺(jué)效果,使人獲得視覺(jué)上的審美愉悅。
篇13
宋代最高統(tǒng)治者提倡以文治天下,政治上雖未達(dá)到預(yù)期的文治效果,但卻造就了一個(gè)相對(duì)繁榮的文化時(shí)代,成就了一批文人志士。理學(xué)的發(fā)展是宋代文化的一個(gè)亮點(diǎn),雖不能肯定地說(shuō)理學(xué)肇始于宋代,但卻是集大成于這個(gè)時(shí)期。宋以前,宗教極為盛行,唐代三教鼎立,其中道教沿南北朝以來(lái)的符箓、丹鼎二派發(fā)展,而佛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師承,其著作也大量涌現(xiàn);為了與佛、道抗衡,儒學(xué)兼取南北經(jīng)學(xué)流派,并進(jìn)一步發(fā)掘傳統(tǒng)儒學(xué)中深層次的東西,促使孔子儒學(xué)發(fā)展到了一個(gè)更適應(yīng)社會(huì)發(fā)展需要的新高峰。①新儒學(xué)把自然規(guī)律主體化、倫理道德本體化,構(gòu)建了以自然、社會(huì)、人生為一體,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的哲學(xué)體系。入宋以后三教思想修養(yǎng)方式發(fā)生了變化,理學(xué)逐漸興盛,并開(kāi)始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宋初三先生”孫復(fù)、胡瑗、石介認(rèn)為“明體達(dá)用”,開(kāi)理學(xué)之先聲。其中影響更大的理學(xué)代表人物周敦頤、邵雍都引道教思想入理學(xué),又將宋初處于轉(zhuǎn)變中的佛、道修養(yǎng)方式、目的、對(duì)象移入新儒學(xué)。隨后理學(xué)經(jīng)二程、朱熹、陸九淵等人的發(fā)展,得以大成,“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理學(xué)貫穿了宇宙論與倫理學(xué),又因其“在世間”的地位區(qū)別于佛、道,故理學(xué)對(duì)知識(shí)界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guó)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周易大傳·說(shuō)卦》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宋學(xué)家們認(rèn)為必須先就天下之物研究所有道理,然后才能達(dá)到心性的自我認(rèn)識(shí)。從宋代初年起就有一批文人志士堅(jiān)信只要對(duì)事物進(jìn)行精深透徹的研究,就能夠達(dá)到對(duì)于宇宙原理的了解,這就是理學(xué)中“格物致知”的原則。這一原則介入繪畫領(lǐng)域成就了宋代繪畫極端寫實(shí)主義的高峰,同時(shí)由蘇軾所倡導(dǎo)的寫意文人畫也受北宋理學(xué)的影響,其思想之中產(chǎn)生出了諸多富于哲學(xué)意味的理論。而理學(xué)在其后的發(fā)展,無(wú)論是程朱理學(xué)和陸王心學(xué),也無(wú)論是后來(lái)兩派互相滲透而出現(xiàn)的朱陸合流的趨勢(shì),都支持了蘇軾所倡導(dǎo)的文人畫的藝術(shù)思想。
二、畫學(xué)之言“理”
理學(xué)在宋代文化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精神也就不自覺(jué)地滲透到文化的各個(gè)支脈中。頗受宋代統(tǒng)治階級(jí)關(guān)懷的繪畫藝術(sh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學(xué)思想的影響。中國(guó)繪畫在此間出現(xiàn)了兩種發(fā)展趨勢(shì)——寫實(shí)主義和寫意主義,這都與理學(xué)的一些思想有著剪不斷的淵源。“理”在中國(guó)古代畫論中,含義是寬泛而多變的,有時(shí)指道理,有時(shí)指哲理,有時(shí)物理連用,有時(shí)地理連通,有時(shí)以文理、神理、至理……出現(xiàn),這使“理”字不能達(dá)詁,也使后學(xué)者仁者見(jiàn)仁、智者見(jiàn)智,提供了各種不同解說(shuō)的可能。總的來(lái)說(shuō),在宋代繪畫中,“理”大體涵蓋兩個(gè)層次,一是自然世界中,事物所遵循的、客觀存在的、科學(xué)的規(guī)律,即《莊子·養(yǎng)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文中的“依乎天理”的“理”,即必然規(guī)律和法則。二是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人所依從的、由人文社會(huì)內(nèi)省而逐漸形成的,主觀上的某些既成的規(guī)定。如不同民族有各自的風(fēng)俗習(xí)慣一樣,并非先天就具有這種規(guī)律,而是后天形成的一種原則。第一種“理”,如同科學(xué)一樣,是可探索卻不可改變的理,是事物外在表現(xiàn)和內(nèi)在規(guī)律的整體體現(xiàn)。第二種“理”在宋代繪畫中尚處于自我完善的發(fā)展階段,主要表達(dá)于文人畫中,屬于一種情理。
1.寫實(shí)主義繪畫中的“理”
歷代畫家一直在為寫實(shí)而究物之“理”,到宋代達(dá)到高峰。我們知道,宋代的儒者是最為忠實(shí)的自然觀察者。在中國(guó)古代,宋代文人對(duì)自然界的了解非常細(xì)致深入,對(duì)自然界也親和貼近,宋代繪畫是用極端的寫實(shí)主義傾向來(lái)表達(dá)這種科學(xué)的探詢精神的。寫實(shí)就是求真,那么合自然之“理”這一要求必在其中,沈括曾在《夢(mèng)溪筆談》中記載過(guò)這樣一件事:“歐陽(yáng)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jiàn)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shí)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zhǎng),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筆意也。”宋代文人畫的倡導(dǎo)者蘇軾在論及文人畫之外的其他繪畫時(shí),也使用了極端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這些都說(shuō)明宋初繪畫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氣十分盛行。蘇軾在《東坡題跋》中說(shuō):“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shù)。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ài),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jiàn)之,拊掌大笑日:‘此畫斗牛也,斗牛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斗,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yǔ)有云:‘耕當(dāng)問(wèn)奴,織當(dāng)問(wèn)婢。’不可改也。”又說(shuō):“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wú)兩展者。’驗(yàn)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wù)學(xué)而好問(wèn)也。”北宋宮廷繪畫更是將這種自然之“理”體現(xiàn)到了極致,《畫繼》記載:“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jié)實(shí),喜動(dòng)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招畫院眾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燦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腳。上日:‘未也。’眾史鄂然莫測(cè)。后數(shù)日,再呼問(wèn)之,不知所對(duì),則降旨日:‘孔雀升高,必先舉左。’眾史駭服。”2.文人畫之“理”
這種窮自然之“物理”的風(fēng)尚并非只存在于寫實(shí)主義繪畫中,文人畫也是它的一種體現(xiàn)形式,只不過(guò)寫實(shí)繪畫對(duì)事物外在之“理”上表現(xiàn)得更多一些,并借助對(duì)事物外在寫真之“理”達(dá)到對(duì)內(nèi)在“事理”的挖掘。文人畫主張不求形似,但并未忽視事物內(nèi)在之“理”,它是將事物內(nèi)在之“理”從特殊化為一般,以文化人的身份與手法將其凝聚起來(lái),并通過(guò)文人不求形似的繪畫方式將其表達(dá)出來(lái)。
文人畫“畫意不畫形”的倡導(dǎo)者蘇軾,論畫總是言“意”說(shuō)“理”,如《書吳道子畫后》《跋吳道子地獄變相》都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之語(yǔ),其在《坡全集·凈因院畫記》中更將“常理”與“常形”對(duì)舉,且頗有“一物須有一理”的意味:“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煙云,雖無(wú)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dāng),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盜名者,必托于無(wú)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dāng),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wú)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jǐn)也。”②這里的“理”,是形式創(chuàng)造的先導(dǎo),指客觀事物的內(nèi)部規(guī)律,即生命的自然構(gòu)造、運(yùn)行變化和由此產(chǎn)生的自然無(wú)常的情態(tài)。因?yàn)樽匀唤缰性S多可視之物是“無(wú)常形”的,如“山石竹木水波煙云”,其形態(tài)會(huì)隨時(shí)間、地點(diǎn)、天氣等條件發(fā)生變化,但這些事物是有“常理”的,再變也有一定的規(guī)律。只有深入體會(huì)這些客觀事物的變化規(guī)律,才能將物象的活的精神凝聚于筆墨形式之間。在蘇軾看來(lái),“常形”之失不算大毛病,而“常理”之失則會(huì)導(dǎo)致整幅畫的格調(diào)和氣韻都隨之不復(fù)存在,他把對(duì)“理”的重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韓拙也在《山水純?nèi)ふ撚^畫別識(shí)》中說(shuō):“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眾,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縑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dá)是理也。”張懷在《山水純?nèi)ず笮颉分幸嘤姓撌觯骸岸藶槿f(wàn)物最靈者也,故人之于畫,造乎理者,能盡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性之機(jī)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jī)者至神之用,機(jī)之一發(fā),萬(wàn)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huì)神融,默契動(dòng)靜,揮一毫,顯于萬(wàn)象,則形質(zhì)動(dòng)蕩,氣韻飄然矣。故昧于理者,心為緒使,性為物遷,汩于塵坌,擾于利役,徒為筆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語(yǔ)天地之真哉!”文人畫主張的寫意,是通過(guò)依“理”而化特殊為一般來(lái)完成的。因“理”而化的形,并不曾離開(kāi)形,但比一般的形簡(jiǎn)明扼要,有生動(dòng)之致、無(wú)細(xì)碎之弊,能夠幫助觀察者明察秋毫、糾正不辨輿薪之謬,這是合乎天然的藝術(shù)概括。梁楷畫的《潑墨仙人圖》,雖然造型狂怪、筆墨放縱,然而揣摩起來(lái)卻合情理。這種“怪而不怪”,實(shí)際上就是文人畫體現(xiàn)的以“理”為依據(jù)幻化物形和筆墨的法度,目的是使畫面更傳神,更能抒畫家胸中逸氣,這是藝術(shù)達(dá)到化境的一種表現(xiàn)。
在蘇軾的倡導(dǎo)和啟發(fā)之下,士大夫畫家們苦心孤詣地探索,在形似與神似、寫實(shí)與寫意、主觀與客觀中尋求其平衡的支撐點(diǎn),使畫家與觀者之間能突破對(duì)象的表象而進(jìn)行心靈的交流,提高了繪畫的審美境界。宋實(shí)繪畫和寫意繪畫都以能表現(xiàn)事物內(nèi)在之“理”為最高宗旨,不同的是前者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寫真手法,后者則采用了當(dāng)時(shí)文人提倡的“不以形似”為準(zhǔn)的寫意手法。
三、“理”在宋代繪畫中的發(fā)展
北宋后期,隨著理學(xué)的發(fā)展,文人畫開(kāi)始出現(xiàn)內(nèi)省態(tài)勢(shì)。宋學(xué),無(wú)論何種派別,研究的中心不外乎“人性”與“天理”。朱熹說(shuō)“心與理一”“一心具萬(wàn)里”。③到了陸九淵那里,則發(fā)展成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wàn)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④宋代中后期,理學(xué)家們對(duì)于研究世界可以獲得真理的信念開(kāi)始動(dòng)搖,認(rèn)為求知的目的不在宇宙的終極真理而在于人自身。理學(xué)的發(fā)展也愈來(lái)愈趨向于內(nèi)省,愈來(lái)愈憑直覺(jué)來(lái)把握事物之理,這種信念支配了其后數(shù)百年的學(xué)術(shù)思想,也為宋以后文人畫的漸趨成熟提供了思想憑借。⑤這時(shí)在文人畫中,多了些“情理”,文人畫不僅體現(xiàn)事物內(nèi)在的物理、妙理,而且成為張揚(yáng)畫者內(nèi)心性情的一種手段,更強(qiáng)調(diào)畫家的主觀感情與客觀物象的有機(jī)結(jié)合,開(kāi)始將藝術(shù)美指向內(nèi)心。這也就是文人畫在元代達(dá)到時(shí)“不過(guò)逸筆草草,聊以寫胸中逸氣耳”的前兆。文人畫家們不僅以體現(xiàn)物之“內(nèi)理”為己任,更追逐于自我價(jià)值的表現(xiàn),使自己的作品更能夠抒情達(dá)意,體現(xiàn)自我。蘇軾的《枯木竹石圖卷》看似荒怪,但是不論從物形還是從物性看都是合乎“物理”的,此圖是表現(xiàn)畫家內(nèi)心“郁結(jié)”的典型之作。再如他畫的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看似隨心所欲,其實(shí)是他經(jīng)常觀察竹自寸萌之時(shí)起,至劍拔十尋迎風(fēng)傲立止,節(jié)葉皆生而有之的生長(zhǎng)過(guò)程,再融入他自己仕途多舛而傲然不屈的心情后才形成的畫法。石濤曾批評(píng)他的畫說(shuō):“東坡畫竹不作節(jié),此達(dá)者之解,其實(shí)天下不可廢者,無(wú)如節(jié)。”這是石濤深受亡國(guó)之恨,強(qiáng)調(diào)氣節(jié)才發(fā)的議論。頌揚(yáng)氣節(jié)也在文人畫的“情理”之中,如宋代文人畫家在花鳥畫上一般都逃脫不了梅、蘭、竹、菊等這些人格寫照的繪畫題材,常常借助這些題材來(lái)體現(xiàn)自己超凡脫俗的人格。郭若虛就認(rèn)為文同的墨竹寫出了神韻和性格:“文同……善畫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fēng)可動(dòng),不筍而成者也。”⑥由此可見(jiàn),宋代文人畫的理學(xué)精神已經(jīng)開(kāi)始從關(guān)注外在事物規(guī)律轉(zhuǎn)向內(nèi)在人文關(guān)懷,以體現(xiàn)人的主觀情感為最高追求,這也正是宋代后期寫實(shí)繪畫跨越高峰走向曲終雅奏、寫意畫漸趨高漲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因素。
繼蘇軾以后。宋代繪畫把“理”提高到一個(gè)新的高度,即“理”以前是為儒家寫實(shí)主義服務(wù)的,以形似的“真”來(lái)達(dá)到教化的作用。后來(lái),繪畫抒情達(dá)意的作用日漸抬頭,則“理”又為達(dá)到內(nèi)質(zhì)外形的融通服務(wù),這是一個(gè)很自然的過(guò)程。“理”的作用并沒(méi)有被減弱,而且在抒情寫意為基本審美趣味的繪畫中,“理”反而成了主客觀對(duì)話的重要中介。
注釋:
①鄧喬彬.中國(guó)繪畫思想史.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第358頁(yè).
②同上,第360頁(yè).
③朱熹.語(yǔ)類卷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