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這首耳熟能詳的山西民歌讓人們對走西口這個歷史文化現象不再陌生。從明末清初至今,走西口的山西人從未間斷,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帶著親人的囑托,毅然離開家鄉,去口外尋找希望與財富。走西口的歷史是一部名聞天下的移民史,晉商在走西口的大潮中,在血淚和辛酸中書寫著輝煌。
本書通過對走西口的歷史成因、具體移民路線和主要參與人群等進行描述,以及對西口位置進行具體界定,梳理了走西口的歷史發展脈絡。此外,全書從多個維度詳細介紹了走西口現象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走西口文化的異化與傳承和走西口精神對于當今社會的積極影響,從而強調了走西口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劉建生,男,1956年1月生,山西右玉殺虎口鎮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山西省教學名師,省委聯系專家。現任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所長,兼山西省晉商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常務理事、近代史專業委員會副會長,當代山西研究會常務理事,山西省研究系列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山西省高級經濟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山西省學位委員會社科評審組成員,山西省教育廳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經濟管理學科評審組成員。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山西省社科、軟科學項目11項,共發表論著300余萬字,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軟科學》、《中國地方志》、《清史研究》等、省級刊物150余篇。主要代表著作有《明清晉商制度變遷研究》、《明清晉商信用制度變遷研究》、《山西典商研究》、《晉商研究》、《山西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稿》、《回望晉商》等。曾獲山西省社科成果一等獎、二等獎,省教學成果一等獎,省史志編纂成果一等獎,省社科成果應用推廣二等獎,北方十五省(市)哲學社會科學圖書獎。曾獲山西省教師、省"三育人"先進個人、太原市精神文明先進個人等稱號。
及時節勇往直前的靈魂
歷史上"走西口"的移民范圍廣泛,主要來自山西西北部的保德、偏關和河曲三縣,屬于山西省雁北地區的平魯、朔縣、右玉、左云、山陰等縣,陜北的府谷、神木、靖邊、橫山、榆林、定邊六縣和河南、甘肅的部分地區。"走西口"活動穿越了三個世紀之久。
一、春去秋歸"雁行客"
清朝建立之初,統治者對蒙古地區防范較嚴。他們一方面采取一系列羈縻政策,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來加強對蒙古民族的統治,另一方面嚴厲禁止漢民到口外墾殖,對膽敢招募漢民的蒙古官員和越境到口外種地的漢人進行非常嚴厲的懲處。《欽定理藩部則例》中記載:凡蒙古官民私招漢民去種地的,要扣罰俸祿,有違反的竟扣8年俸祿,直至革職;罰牲畜,最多罰72頭,打皮鞭,最多打100皮鞭,往往是罰打一并施行;戴木枷坐牢9個月,甚至充軍。如果漢人私自到蒙古草原開荒種地,要戴枷治罪,甚至發配到4000里以外的邊疆去充軍。
隨著清王朝統治地位的日趨鞏固,對蒙古民族的防范也就日漸松懈,漢人也得以隨著蒙古草原的逐漸開放而進入蒙古腹地。入蒙古草原的漢人是被稱為"綠營軍"的一群人,他們是清王朝收編的明末農民起義軍部隊的一部分。作為地方治安部隊,有一部分駐在內蒙古,為了區別于八旗兵士而打著綠色的旗幟,故得名。綠營軍為解決軍糧就在營區開荒種地,部隊開拔之后,剩下的熟地就招募漢人種植。漢族的一般窮苦百姓就是這樣得以進入蒙古草原的。后來隨著綠營軍駐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漢民開始到"口外"謀生。
到了康熙朝,隨著邊外蒙古社會秩序的逐漸趨于穩定,牧區出現了"牲口繁息,生計豐饒"的經濟復蘇景象。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單純的游牧經濟已不能滿足牧民生活多樣化的需求,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口外蒙古地區人民生活困窘的狀況。而且每遇災荒,草原上便會出現"青草不生,牛羊倒斃不盡"的狀況,這對以畜牧業為主的口外經濟來說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開墾土地種植莊稼勢在必行。當時蒙古牧民也有人從事農耕,但耕種技術遠較中原地區落后,于是,一些地方官員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上奏"乞發邊內漢人與蒙古一同耕種"。
與此同時,中原地區災荒不斷,給經濟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破壞,再加上八旗貴族在華北地區頒行"圈地令",又使大批內地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這樣,對這些失去田地的口內人來說,口外大片未墾殖土地無疑具有極強的吸引力,一旦限制口內百姓出境墾荒的政策有所松動,大批難民必定從各個關口涌出口外謀生。在這種形勢下,鄂爾多斯貝勒松普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提出的招募內地人合伙種地的請求獲得了朝廷批準。清政府允許在原勘定的50里寬的"黑界地"內劃出20到30里的"白界地"為墾殖界限,招募漢人耕種,歷史上稱之為"開邊"。當時,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清政府對"走西口"民眾有一定的要求,且盤查比較嚴格,所以此時以季節性出邊者居多,他們春出秋回,被稱為"雁行客",人數并沒有大幅度增加。
二、名聞天下之移民潮
雍正以后,清政府雖然仍在嚴厲推行"封禁令",但由于人口增加等諸多因素導致的口內人地矛盾日趨嚴重,所以流民違禁出邊和違禁開墾的現象日益增多,甚至還出現了涌入蒙地的移民潮。移民潮禁之難禁,阻之難阻,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采取了一些權宜之計。
雍正時實行"借地養民"政策,下令內地災民可往口外蒙地開墾土地謀生。乾隆年間又再次重申:"如有貧民出口者,門上不必攔阻,即時出發。"政策的松動使得走西口的人數猛增,到包頭、薩拉齊縣一帶墾荒的人逐漸增多,不少人由"雁行"發展到定居于口外。但是可以看到從康熙"開邊"到乾隆年間,雖允許漢人到鄂爾多斯、后套、土默川等地開墾土地,但防范還是相當嚴密的。
喜歡山西人的精神,這套書很精美
好評,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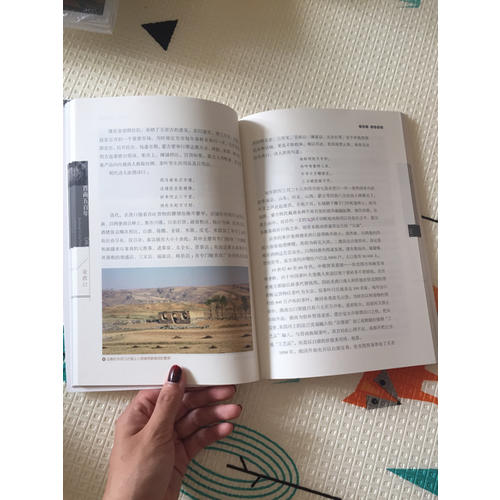 字大,書薄,內容不多。內容還不錯,價格有點偏高
字大,書薄,內容不多。內容還不錯,價格有點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