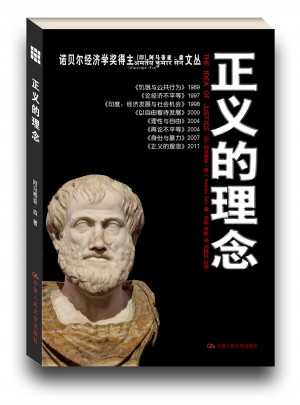
正義的理念
- 所屬分類:圖書 >經(jīng)濟(jì)>經(jīng)濟(jì)通俗讀物
- 作者:(印)[阿馬蒂亞·森] 著,[王磊],[李航] 譯,[劉民權(quán)] [校]譯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hào):9787300154923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 出版時(shí)間:2012-06
- 印刷時(shí)間:2012-06-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shù):--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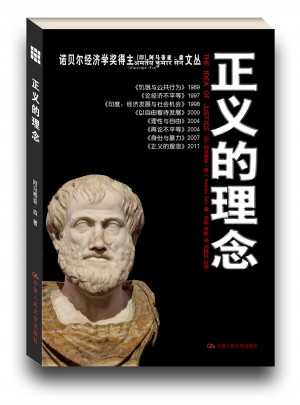
《正義的理念》是自《正義論》(約翰·羅爾斯著)問世以來,有關(guān)正義的最重要的論著。我們?yōu)槭裁葱枰x的理論?我們需要一個(gè)什么樣的正義理論?阿馬蒂亞?森認(rèn)為:我們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對于不公正的直觀感受上;我們必須通過理智的審思來對我們?nèi)粘8惺艿降牟还M(jìn)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確定我們目睹的悲劇是否可以成為譴責(zé)的依據(jù),才能將不可抗阻的災(zāi)害與本可預(yù)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禍區(qū)分開來,才能將我們的視野由對于慘狀的單純觀察和施救,轉(zhuǎn)向?qū)τ谄渲胁还F(xiàn)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 森還明確指出,研究正義問題,需要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問題,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規(guī)則上的探討上;需要關(guān)注如何減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尋找的公正;我們的視野可以遍布全球,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某個(gè)國家的邊界范圍以內(nèi)。任何人都不應(yīng)該也沒有必要把正義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自由、民主和人權(quán)思想貼上西方世界的標(biāo)簽。
阿馬蒂亞?森的正義理念:
● 我們需要尋找的并非是的正義,而是致力于減少明顯的非正義。
● 正義需要關(guān)注實(shí)際的生活與現(xiàn)實(shí),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規(guī)則上
● 正義需要允許多種不同的正義緣由的同時(shí)存在,而不是只允許一種正義緣由的存在。
● 正義應(yīng)強(qiáng)調(diào)公共理性和反思,而不是尋找一成不變的公理性答案。
● 正義需要"開放的中立性",需要超越地方、國家的邊界,在全球范圍內(nèi)評價(jià)一國內(nèi)部的公正。
被譽(yù)為"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良心"、"窮人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力作,關(guān)注弱勢群體的利益,提出了消除顯見的不公平和非正義的方法。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98年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森1933年生于印度,現(xiàn)在仍然保留印度國籍。他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學(xué)學(xué)業(yè)后赴劍橋大學(xué)就讀,1959年取得博士學(xué)位。森曾執(zhí)教于倫敦經(jīng)濟(jì)學(xué)院、牛津大學(xué)、哈佛大學(xué)等著名學(xué)府,現(xiàn)任劍橋大學(xué)三一學(xué)院院長。
森的突出貢獻(xiàn)表現(xiàn)在五個(gè)領(lǐng)域內(nèi),分別是:社會(huì)選擇理論、個(gè)人自由與帕累托的關(guān)系、福利與貧困指數(shù)衡量、饑荒問題與權(quán)利分配不均的關(guān)系以及道德哲學(xué)問題等。
森的學(xué)術(shù)思想繼承了從亞里士多德到亞當(dāng)?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遺產(chǎn)。他深切關(guān)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難的人們,被譽(yù)為"經(jīng)濟(jì)學(xué)良心的肩負(fù)者"、"窮人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森的思想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聯(lián)合國的《人類發(fā)展報(bào)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論框架設(shè)計(jì)的。1972年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得主肯尼斯?阿羅認(rèn)為,"在社會(huì)選擇、福利經(jīng)濟(jì)學(xué)基礎(chǔ)理論、更廣泛的分配倫理學(xué)以及與這些領(lǐng)域相關(guān)的測量問題上。森是一位無可懷疑的大師。"
及時(shí)部分 正義的要求
第1章 理智與客觀
第2章 羅爾斯及其超越
第3章 制度與人
第4章 聲音與社會(huì)選擇
第5章 中立與客觀
第6章 封閉的中立性與開放的中立性
第二部分 理智思考的形式
第7章 位置、相關(guān)性和幻象
第8章 理性與他人
第9章 中立緣由的多元性
第10章 現(xiàn)實(shí)、后果與主體性
第三部分 正義的實(shí)質(zhì)
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
第12章 可行能力與資源
第13章 幸福、福利與可行能力
第14章 平等與自由
第四部分 公共理性與民主
第15章 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
第16章 民主的實(shí)踐
第17章 人權(quán)及其全球性
第18章 公正與世界
譯者前言
一
阿馬蒂亞?森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xué)者,著述甚豐。他因?qū)Ω@?jīng)濟(jì)學(xué)所作的重要貢獻(xiàn)而被授予1998年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其著作在那之后被陸續(xù)介紹到中國。已經(jīng)出版的漢譯專著就有商務(wù)印書館的《貧困與饑荒:論權(quán)利與剝奪》、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的《論經(jīng)濟(jì)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查》、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的《集體選擇和社會(huì)福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的《慣于爭鳴的印度人:印度人的歷史、文化與身份論集》,以及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的《以自由看待發(fā)展》、《理性與自由》和《身份與暴力:命運(yùn)的幻想》等。這些作品大都橫跨經(jīng)濟(jì)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法學(xué)、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等多個(gè)領(lǐng)域,不僅體現(xiàn)了森的廣泛涉獵和深厚積累,更表明了森對于貧困、饑荒、剝奪、不平等等世界范圍內(nèi)普遍存在的社會(huì)現(xiàn)象,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自由、人權(quán)、民主與正義等理論問題的深切關(guān)注和嚴(yán)謹(jǐn)思考。
在本書中,森對以往所作的研究進(jìn)行了的總結(jié)和提煉,并系統(tǒng)地將其納入關(guān)于正義問題的理論框架,那就是:我們?yōu)槭裁葱枰粋€(gè)正義的理論,以及需要一個(gè)什么樣的正義理論。關(guān)于為什么需要一個(gè)正義的理論,即為什么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對于不公正的直觀感受上這一問題,他的回答是:這是因?yàn)槲覀儽仨毻ㄟ^理智的審思來對感官信號(hào)進(jìn)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確定我們目睹的悲劇是否可以成為譴責(zé)的依據(jù),才能將不可抗阻的天災(zāi)與本可預(yù)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禍區(qū)分開來,才能將我們的視野由對于慘狀的單純觀察和施救,轉(zhuǎn)向?qū)τ谄渲胁还F(xiàn)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森同時(shí)承認(rèn),這個(gè)世界上存在諸如歧視、迷信等非理智,但理智的運(yùn)用可以消除或減少這些仍然以某種理智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非理智。而回避理智的人,往往都是手握公權(quán)的衛(wèi)道士。這也與森的正義思想(即我們并非尋找的正義,而是致力于減少明顯的非正義)相一致。
關(guān)于需要一個(gè)什么樣的理論,森明確指出,正義問題所需要的是這樣一個(gè)框架,即:關(guān)注實(shí)際的生活與現(xiàn)實(shí),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規(guī)則之上;關(guān)注如何減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尋找的公正;可以遍布全球,而不只是局限于某個(gè)國家的邊界范圍以內(nèi);允許多種不同的正義緣由同時(shí)存在,而不是只允許一種正義緣由存在。基于此觀點(diǎn),森選擇從現(xiàn)實(shí)切入,通過公共理性的視角在全球范圍內(nèi)來界定正義的原則。事實(shí)上,這種基于理性來認(rèn)識(shí)正義的方法論與世界觀并非僅源于西方世界的傳統(tǒng),在諸如古印度等世界其他地方早已有之;也不是人類思想史上僅有的一次選擇,因?yàn)榭v觀古今,都可以看到著眼于制度安排的先驗(yàn)主義與著眼于現(xiàn)實(shí)的比較主義這兩種觀念之間的并存與對抗。
下面將對本書的要點(diǎn)進(jìn)行歸納和闡發(fā),以便讀者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本書的主旨與邏輯。將對譯文中的某些表述作必要的說明和詮釋,以方便讀者的閱讀。
二
本書共分四個(gè)部分。及時(shí)部分內(nèi)容是正義的要求,即推進(jìn)正義所需要的理智是什么這一問題。森指出,對公正與非公正問題需要進(jìn)行客觀的思考,而這種客觀性需要依靠理智來進(jìn)行道德評判。選擇理智的審思并不在于它必然能保障作出正確的判斷,而在于它能使我們盡可能地客觀。亞當(dāng)?斯密提出的"中立的旁觀者"為理智提供了一種實(shí)現(xiàn)方式,即需要引入遠(yuǎn)近不同經(jīng)歷的多種觀點(diǎn)和視角,通過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來審視自己的感受。這就使得公正的原則可以具有多樣性,而不必根據(jù)剛性的單一原則來確定;也使得我們可以通過理智來審視包括情感在內(nèi)的許多不同緣由,以尋求尊重與包容,從而避免理智淪為草率且不當(dāng)?shù)淖载?fù),或者局限于冰冷無情的算計(jì)。由于所有人都能通過開放地接納信息反思來自不同地方的觀點(diǎn),并采取互動(dòng)的思辨來討論如何看待背后隱藏的問題,以此達(dá)到理智,因此無論是一般地對于民主政治而言,還是具體地對于追求社會(huì)公正而言,不受限制的公共理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由于理智的實(shí)踐性和開放性,森在肯定了羅爾斯正義論的重要貢獻(xiàn)后,也對這一正義理論的奠基之作提出了批評。及時(shí),在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中,幾乎只對抽象的"公正制度"予以直接的關(guān)注,卻不那么關(guān)心具體的"公正社會(huì)",而后者同時(shí)取決于有效的制度和實(shí)際的行為方式。長久以來,人們在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分析中都將實(shí)現(xiàn)公正等同于尋找正確的制度結(jié)構(gòu)。然而,事實(shí)表明,這些宏偉的制度方案都未能實(shí)現(xiàn)其愿景,它們能否產(chǎn)生好的社會(huì)結(jié)果有賴于各種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政治及文化狀況。如何把公正原則的運(yùn)作與人們的實(shí)際行為結(jié)合起來,正是對社會(huì)公正進(jìn)行實(shí)踐理性思考的核心,而將制度本身視為公正的體現(xiàn),只會(huì)使我們陷入某種形式的制度原教旨主義。第二,羅爾斯所采用的社會(huì)契約方法,無可避免地將追求公正的參與者限定在某個(gè)既定的政體或"民族"之內(nèi),而正義要求無偏頗的中立與客觀。因此,羅爾斯所采用的是"封閉的"中立性,即將觀點(diǎn)與關(guān)注所涉及的范圍圈定在一個(gè)主權(quán)國家的成員之中,由某個(gè)社會(huì)或國家的成員作出中立的判斷。相反,"開放的中立性"指的是,由于彼此之間無論遠(yuǎn)近所負(fù)有的相互義務(wù)、通過各種渠道形成的相互依賴,以及為了避免地域性的偏見,中立的評價(jià)應(yīng)該包括來自所關(guān)注的群體之外的判斷。因此,我們無疑需要超越國家的邊界,在全球范圍內(nèi)評價(jià)一國內(nèi)部的公正。
在此基礎(chǔ)上,森進(jìn)一步提出了他所主張的社會(huì)選擇理論。社會(huì)選擇程序采取的形式是:從某種"社會(huì)視角"出發(fā),根據(jù)相關(guān)主體的評價(jià),對不同的社會(huì)狀態(tài)進(jìn)行比較。因此,社會(huì)選擇理論關(guān)注事物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先驗(yàn)的制度;允許存在不完整的排序,而并非尋求面面俱到的方案;認(rèn)識(shí)到存在多種合理的,而不是正確的判斷原則;強(qiáng)調(diào)公共理性和反思,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公理性答案。這就與霍布斯、羅爾斯以及諾齊克等人基于契約方法的公正理論具有根本的不同,因?yàn)槠跫s方法實(shí)際上是在尋找一種并不存在的"公正制度",并假設(shè)一旦契約達(dá)成,人們的實(shí)際行為將會(huì)遵循契約運(yùn)轉(zhuǎn)所要求的規(guī)范。
三
本書的第二部分內(nèi)容是推理的形式,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理智思考可以怎樣進(jìn)行。首先是理智思考的視角。既然我們所能看到的事物,與我們站在何處、想要看到什么是相關(guān)的,并且也將反過來影響我們的信仰、認(rèn)識(shí)和決定,那么在政治和道德評價(jià)中,就需要特別注意所處位置對于我們所作的判斷可能產(chǎn)生的潛在影響。尋找某種客觀中立的的認(rèn)識(shí),是探討道德倫理問題的核心所在。盡管我們對世界的整個(gè)認(rèn)識(shí)都建立在現(xiàn)有的感知和所產(chǎn)生的思想上,而我們的感知與思想依賴于我們有限的生理感官,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以更的視野來部分或者克服位置所帶來的局限。我們一方面可以通過合理地選擇比較對象,而不是先驗(yàn)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來盡可能地避免位置產(chǎn)生的局限對我們判斷的影響,另一方面通過開放的中立性,來較大限度地拓寬我們的視野。
其次,理智思考的內(nèi)容究竟是什么。理性選擇理論將行為的所有動(dòng)機(jī)都?xì)w于追求自身利益,這或是與他人無關(guān)的自利,或是關(guān)注了其他人的利益但也間接提升了自己的福利。對此,森認(rèn)為,我們可以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有說服力的方式來描繪理性選擇,即將我們的選擇置于一種可持續(xù)的理智思考的基礎(chǔ)之上。當(dāng)某個(gè)選擇的緣由是頭腦中已有的經(jīng)驗(yàn)或習(xí)慣時(shí),我們通常可以合理地采用這種選擇。因此,理智思考,或者說廣義的理性實(shí)際上是一種相當(dāng)包容的準(zhǔn)則,它可包括多種不能"合理地拒絕"的緣由,這不僅限于有意識(shí)的自利,而且包括并非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標(biāo),如對于合理的行為規(guī)則的尊重,考慮他人的愿望與追求,抑或公平地對待他人的行為準(zhǔn)則,等等。
正是因?yàn)槔碇撬伎伎梢园荻喾N緣由,所以即使是在基于現(xiàn)實(shí)后果的考量中,也并不意味著對于結(jié)果的責(zé)任感和對于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考量就被排除在外。通過對于古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中一個(gè)戰(zhàn)役的分析,森認(rèn)為,一個(gè)人不僅有充分的理由去注意某個(gè)具體選擇會(huì)帶來的后果,而且有足夠的理由從一個(gè)充分寬廣的角度來看待與之相關(guān)的各種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包括相關(guān)的主觀責(zé)任感、所采用的過程以及人與人的關(guān)系,這也是考慮到各方面相關(guān)因素的"結(jié)果"與只著眼于最終結(jié)果的"終極結(jié)果"之間的區(qū)別。而無論是著眼于最終結(jié)果的緣由,還是涉及上述責(zé)任、過程與關(guān)系的緣由,對其相關(guān)性和重要性的評價(jià)都需要接受個(gè)人或者公共理性的審思。
四
本書的第三部分在對理智,這一推進(jìn)正義所必須具備的要素進(jìn)行了分析之后,森開始進(jìn)入正義的實(shí)質(zhì)層面。他分別從自由,以及與自由相聯(lián)系的可行能力一方,和以資源與幸福為代表的另一方,來考察他們各自對于正義的標(biāo)準(zhǔn),也就是進(jìn)行政治和道德評價(jià)的意義。森指出,在評價(jià)生活的時(shí)候,我們有理由不僅對能過上什么樣的生活發(fā)生興趣,而且關(guān)注在不同生活方式之間進(jìn)行選擇的自由。自由之所以重要,至少是出于機(jī)會(huì)和過程兩方面的原因。及時(shí),更大的自由使我們有更多的機(jī)會(huì)去獲得所珍視的事物。第二,更大的自由也意味著我們可以不受他人施加的限制,而決定自己要去獲得的事物。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gè)背景下來研究,即僅從一個(gè)人事實(shí)上的最終選擇,也就是"終極結(jié)果"的角度,還是應(yīng)同時(shí)考慮到更寬廣的選擇過程,尤其是考慮到他可能作出的其他選擇,也就是"結(jié)果",來對一個(gè)人能過上他所珍視的生活的能力進(jìn)行評價(jià)。
可行能力就這樣與自由和正義聯(lián)系在了一起。由于可行能力的概念是以自由和機(jī)會(huì),即人們選擇不同類型的生活的能力為導(dǎo)向的,而不是僅僅著眼于最終的選擇或結(jié)果,因此可行能力視角能夠反映人與人之間在各自所具有的優(yōu)勢上的明顯差別,而這種差別可以幫助我們認(rèn)識(shí)到一個(gè)人真正的弱勢所在,從而進(jìn)行相應(yīng)的政治和道德評價(jià)。此外,可行能力視角必然會(huì)涉及我們的生活和我們所關(guān)注的事物的多種特征,而不單單只是一些容易計(jì)算的收入和商品,因此可行能力是不可通約的,但這并不會(huì)打亂對于不公正的評價(jià)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樣,我們面臨的主要任務(wù)是通過個(gè)人和公共理性都可以觸及的比較判斷來使事情處在正確的軌道上,而不是必須對所有可能的比較進(jìn)行逐一評價(jià)。
反觀資源視角,由于它著眼于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它與貧困的關(guān)系并非如通常想象中的那么簡單,而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具體的人與其所處的自然和社會(huì)環(huán)境。例如,世界上的六億殘障人口不只受到低收入的困擾,各種不同的情景都使得他們失去了獲得體面生活的自由。盡管羅爾斯也注意到有必要對以基本品為核心的資源方法加以修正,以更好地把握人的實(shí)際自由,但是他對于這個(gè)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的處理方法卻有重大局限,以至于并沒有對其業(yè)已建立的基本制度產(chǎn)生任何影響。同樣,幸福與否有助于判斷人們是否獲得了他們所珍視的和認(rèn)為值得珍視的事物。但這不意味著幸福就是我們珍視事物的緣由。我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反思和相互之間的公開討論,來對我們內(nèi)心深處的信念和對事物的反應(yīng)的性進(jìn)行辨別,從而保障我們沒有被直覺所誤導(dǎo)。對于適應(yīng)了剝奪狀況所產(chǎn)生的滿足和幸福,我們應(yīng)該進(jìn)行更多的思考,只有這樣,已經(jīng)適應(yīng)了剝奪狀況的人們才會(huì)具有反抗的自覺。
因此,森指出,把與主觀能動(dòng)性自由相聯(lián)系的可行能力,僅僅看作一種資源或者福利意義上的個(gè)人優(yōu)勢是錯(cuò)誤的。人與人之間優(yōu)劣勢的比較不能局限于效用、資源或者幸福。對于所遭受的剝奪而產(chǎn)生的適應(yīng)性,會(huì)通過幸福或愿望實(shí)現(xiàn)的方式,導(dǎo)致對效用的扭曲,從而使得長期受剝奪的人并未對其實(shí)際遭遇的困境給予應(yīng)有的重視。因此,在評價(jià)社會(huì)制度的時(shí)候,對于自由的考量應(yīng)被給予實(shí)質(zhì)性的關(guān)注。然而,我們需要將賦予自由某種優(yōu)先性的訴求,與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給自由標(biāo)上字典式的優(yōu)先這種極端要求區(qū)分開來。此外,我們還需要從多個(gè)側(cè)面,而不只是從一個(gè)角度來看待自由。例如,菲利普?佩迪特的自由觀就捕捉到了自由不受依附的一個(gè)方面,而這是可行能力視角下的自由所不能的。這種多元性本身也正是正義理論的一部分。
五
本書的一部分內(nèi)容是正義的實(shí)現(xiàn)方式,即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和作為自由主張的人權(quán)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實(shí)現(xiàn)。當(dāng)我們從公共理性這一更為廣闊的視角,而不僅僅從公共投票這一具體形式來看民主時(shí),可以看到民主不僅只是西方的傳統(tǒng),而且在其他幾個(gè)文明古國都曾經(jīng)存在。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其效用與力量不僅依賴于對歷史傳統(tǒng)和信仰的繼承,也依賴于相關(guān)制度和實(shí)踐所提供的討論與互動(dòng)的機(jī)會(huì)。而推進(jìn)世界上的公共理性所需要考慮的一個(gè)突出問題是支持自由和獨(dú)立的新聞媒體,以賦予受剝奪的弱勢人群表達(dá)的機(jī)會(huì),敦促統(tǒng)治者在自然災(zāi)害面前采取救援措施,以及通過幫助人們更好地認(rèn)識(shí)自己的多元身份,進(jìn)而形成包容的價(jià)值觀。在民主的所有這些方面,積極而又充滿活力的媒體至關(guān)重要。
人權(quán)是一種關(guān)于自由而非利益的道德主張。如果權(quán)利只是建立在利益而不是"自由"的基礎(chǔ)之上,那么我們將不得不思考,參與游行示威是否符合個(gè)人的利益,示威是否可以包括在人權(quán)的范疇內(nèi)。而一項(xiàng)可持續(xù)的道德主張所要求的,是當(dāng)其他人在中立的基礎(chǔ)上對這些權(quán)利主張進(jìn)行審思時(shí),普遍認(rèn)識(shí)到支持這些權(quán)利主張的道理之所在。這樣,在公共理性和民主一方,與自由和人權(quán)一方之間,就產(chǎn)生了緊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因此,與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一樣,推動(dòng)人權(quán)道德的方式和手段并不僅僅局限于制定新的法律。基于溝通、倡導(dǎo)、報(bào)道,以及信息充分的公眾討論的重要性,人權(quán)無須依賴于強(qiáng)制性立法就可以產(chǎn)生影響。
因此,人權(quán)也可以是一種不義務(wù)。如果自由被認(rèn)為是重要的,那么人們就有理由問,他們應(yīng)該做些什么來幫助彼此捍衛(wèi)和推動(dòng)各自的自由。這里的基本義務(wù)是,一個(gè)人必須認(rèn)真思考在考慮到他人自由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以及自己的情況和可能的效果的前提下,可以做些什么來幫助他人實(shí)現(xiàn)其自由。與這種考量相關(guān)的行為選擇,必須根據(jù)優(yōu)先選擇、權(quán)重以及評價(jià)框架來考慮很多不同的情況。因此,關(guān)于義務(wù)的具體內(nèi)容可以存在一些模糊性,而這與法定權(quán)利的明確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不義務(wù)的特點(diǎn)并未降低道德主張的地位,因?yàn)橐粋€(gè)規(guī)范性的理智思考的框架可以合理地允許各種不同情形的存在,而這些是難以置于明晰的法律框架之中的。
無論是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還是作為自由主張的人權(quán),都必須通過超越國界的開放審思來獲得客觀性,而這也是本書正義理論的核心特征。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實(shí)現(xiàn)民主和人權(quán)的全球性就不再是遙遙無期的事情,也不再需要以一個(gè)全球性國家的存在作為其產(chǎn)生的前提。而這不可避免會(huì)帶來多種"不能合理拒絕"的緣由,也使得理性的結(jié)論可以以部分排序的形式出現(xiàn)。開放的中立性、緣由的多元性,以及方法的比較性,就這樣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gè)既包容又嚴(yán)格的正義理論的基本框架,而不同的正義理論之間,同樣也會(huì)因?yàn)檫@種基于開放性、多元性和比較性的對話和思考,推動(dòng)人類對于善、真和正義的不懈追求。
……
這是自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問世以來,有關(guān)正義的最重要的論著。森提出,在我們這個(gè)動(dòng)蕩不安的世界,我們迫切需要的不是理想中的公正國家的理論,而是使我們作出相對公正的判斷的理論,這個(gè)理論告訴我們在當(dāng)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們什么時(shí)候以及為什么正在接近或遠(yuǎn)離正義的實(shí)現(xiàn)。
——希拉里?帕特南(Hilary Putnam),哈佛大學(xué)
《正義的理念》以清晰易懂、充滿活力的散文形式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政治哲學(xué),這種政治哲學(xué)致力于減少世界上的不公正,而不是憑空建立理想中的公正的空中樓閣。阿馬蒂亞?森使政治哲學(xué)面對人類的渴望以及現(xiàn)實(shí)世界中人類受剝奪的狀況,而他已經(jīng)在為改變這種狀況奉獻(xiàn)其智慧人生。
——G. A.科恩(G. A. Cohen),牛津大學(xué)
本書主要是批評性分析和綜合論述。森包容性的態(tài)度使他超越了許多重要學(xué)者,以及他所分析的這些學(xué)者的觀點(diǎn)。《正義的理念》向?qū)W術(shù)界和政策制定者們呈現(xiàn)了關(guān)于公正重要性的一連串的思考。
——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斯坦福大學(xué)
約翰?羅爾斯這位于2002年辭世的美國哲學(xué)家,森先生以極其謙遜的口吻指責(zé)他將政治思想家們引入了一條曲折的死胡同。森先生抱怨道,羅氏試圖對理想的公正制度進(jìn)行描述,但卻使人無法集中思考社會(huì)的不公正,而且使這種思考徒勞無功。對這位可能是過去一個(gè)世紀(jì)最有影響力的英語國家的政治思想家的猛烈抨擊本身就足以引起世人的關(guān)注。《正義的理念》也是對森先生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理性以及人類福祉的構(gòu)成部分和衡量標(biāo)準(zhǔn)的著述的一個(gè)總結(jié)。
森先生以一本正經(jīng)的詼諧、對歷史的感觸以及無拘束的世界大同主義來寫本書……《正義的理念》是一次盛宴。再也不會(huì)有人有理由抱怨說他不清楚阿馬蒂亞?森偉大理論的各個(gè)組成部分之間的關(guān)系了……森先生恰當(dāng)?shù)匾悦裰髯鹘Y(jié)。他說,民主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但是若是沒有就價(jià)值和原則進(jìn)行公開的辯論,任何一種民主都不可能成功。對于他所稱之為公共理性的這一重要組成部分來說,《正義的理念》為之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xiàn)。
——《經(jīng)濟(jì)學(xué)人》(The Economist)
森是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既有對當(dāng)代重大問題,如身份認(rèn)同和饑荒,浪漫但富有啟發(fā)性的評論,也有關(guān)于政治哲學(xué)的鴻篇巨著。許多人都在思索是否有一個(gè)比信貸危機(jī)之前的世界更好的世界,是否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在這一時(shí)刻,森推出了《正義的理念》,試圖構(gòu)建一種新的方法來理解更加公正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樣的。
如果公共知識(shí)分子是以他或她能否構(gòu)建起跨越純粹理念的世界和影響最深遠(yuǎn)的政策二者之間的橋梁來界定的話,那么很少有人能與森比肩。森革命性的理念是關(guān)于可行能力的,而這是人們生存并選擇如何過上好生活的能力。正義的一個(gè)好的理念就是關(guān)于提升可行能力的。
——戴維?阿羅諾維奇(David Aaronovitch), 《泰晤士報(bào)》(The Times)
《正義的理念》……非常棒,探討棘手的話題,尊重幾個(gè)世紀(jì)以來的哲學(xué)辯論,同時(shí)又有創(chuàng)意地對這些話題重新思考,[它]無疑為日后的社會(huì)研究確定了議程表。《正義的理念》將經(jīng)濟(jì)和政治分析與道德的理性相結(jié)合,這是這本書最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
《正義的理念》而簡練地超越了政治傳統(tǒng)。從前往后讀,這本書是對經(jīng)典的政治理論富于邏輯的再思考;從后往前讀,它是對人們普遍迫切關(guān)注的事情的備忘錄。不管以哪種方式讀這本書,這都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鴻篇巨著。如今政治越來越引人爭議、國家和社會(huì)面臨暴力挑戰(zhàn)、全球性政治參與的規(guī)則難以捉摸(而且常常被忽視),在這樣一個(gè)時(shí)代《正義的理念》是對文明的呼喚,呼喚知識(shí)分子仁愛參與的模式。
——葆拉?紐伯格(Paula Newberg), 《環(huán)球郵報(bào)》(Globe and Mail)
在《正義的理念》中,森將他的許多貢獻(xiàn)和成就轉(zhuǎn)化為他對正義獨(dú)特的看法——很難預(yù)測政治哲學(xué)目前的復(fù)興將如何影響未來的人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辯論對世界和歷史都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森關(guān)于正義、社會(huì)選擇理論以及評估福利的可行能力方法的理念是對它們的重要貢獻(xiàn)。
——塞繆爾?弗里曼(Samuel Freeman), 《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