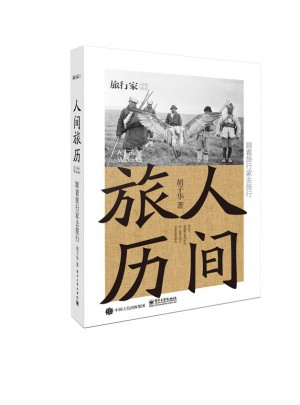
人間旅歷:跟著旅行家去旅行
- 所屬分類:圖書 >旅游/地圖>旅游攻略>旅游小百科
- 作者:[胡子華] 著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9787121295911
- 出版社:電子工業(yè)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7-01
- 印刷時間:2016-11-01
- 版次:1
- 開本:32開
- 頁數(shù):--
- 紙張:純質(zhì)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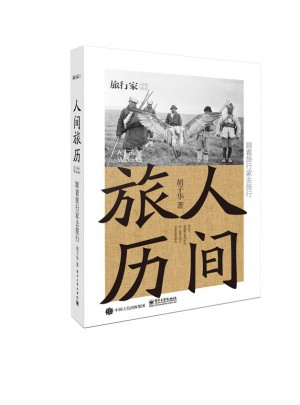
2012年起,胡子華在《旅行家》開設專欄“致敬旅行家”。當時起意做這個欄目的初衷很簡單——世界上那些走在我們前面的杰出的行者,從來未被我們超越。在我們想要啟程之前,多讀讀這些真正的旅行家,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好的學習。小胡在《人間旅歷》自序中寫:“旅行是為了得到結結實實的疲乏,但這種疲乏無法通過苦行獲得,而是通過自我更新。”愿我們在旅途中都有更新與進步!
《人間旅歷》為“旅行家 游觀系列”叢書之一。旅行家雜志1996年創(chuàng)刊,是國內(nèi)及時本專業(yè)旅行雜志。多年來,作家專欄都是《旅行家》最為看重、且分量的內(nèi)容,許多睿智又謙和的旅者在《旅行家》雜志上寫下了這些文字。在旅行變得如此容易的今天,這些文章在當代中國的旅行文本中仍是罕見而珍貴的。他們總能夠在文字中建造一座座宮殿,引出更磅礴的世界,也令人反觀自己的旅行。此次,《旅行家》遴選出其中四位作者的專欄集結成書,并命名為“游觀系列”。游之,觀之。希望以此呈現(xiàn)旅行文本的一種精神傳統(tǒng):游記服務于思想,和世界的現(xiàn)實狀況相關。愿“游觀系列”能給予讀者以興奮、思考,以及對于世界與自我這一亙古話題源源不斷的求索。
文學家的旅行和旅行家的文學,構成這部書的特別意義:世界上那些走在我們前面的杰作的行者,從來未被我們超越。——劉亮程
《人間旅歷》通過文化名人的旅行來看旅行對于現(xiàn)代人的意義,而這些文化名人也通過旅行顯現(xiàn)出了性格、心理、趣味與生活方式。這很有意思。——陳曉明
胡子華在《旅行家》工作期間所寫的這一系列文章,對《旅行家》來說亦是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他所講述的這些真正的旅行家,以及他們所走過的路,對于身處浮華年代、旅游僅止于朋友圈曬圖的我們來說,是一種永恒的提醒。——《旅行家》雜志
胡子華,1985年生,江西婺源人,寫作者,媒體人,2012年起在《旅行家》雜志開設專欄“致敬旅行家”。
自序
文學與旅行 旅行之作家篇:自我并不是那么重要
1夏多布里昂:法蘭西載負我遠行
2雨果:關于歷史的三種視力
3契訶夫:旅行的終身文學債務
4毛姆:為了故事的旅行
5海明威:硬漢旅行與硬漢文學
6斯坦貝克:冷戰(zhàn)下的美蘇漫游
7卡彭鐵爾:怎樣理解美洲大地
8 雷厄姆 格林:失敗的西非大地
9 艾柯:多重世界的漫游
10保羅 索魯:借旅行歸家
11帕慕克:一個人與一座城
記者與旅行 旅行之記者篇: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去吧!
12 羅伯特 拜倫:游走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
13 艾瑞克 紐比:努爾斯坦之旅
14 雷 卡普欽斯基:旅行與大時代
15 馬克 涂立:印度,在不可思議的背后
16 羅偉林:“未來之國”的希望與憂慮
17 羅伯特 D 卡普蘭:從旅行家到政治預言者
冒險家與旅行 旅行之探險家篇:空白地理的機會和野心
18 理查德 伯頓:維多利亞時代的非洲探險
19 華萊士:馬來群島的博物之旅
20 普爾熱瓦爾斯基:殖民時代,一個旅行家的榮耀與丑聞
21 奧勃魯切夫:中亞尋寶之旅
22 密語、易容術、空行母:大衛(wèi)?妮爾的藏地傳奇
23 洛克:中國大地之旅行淘金
24 T E 勞倫斯:游走中東的帝國書記員
25 羅杰斯:旅行與投資的雙面?zhèn)髌?/p>
學者與旅行 旅行之學者篇:學著接受地方性知識
26馬林諾夫斯基:將旅行帶入人類學
27 曼德拉旅行記
28 格爾茨:旅行的可解方程式
29 桑塔格:跟真實事物在一起
30 西蒙 沙瑪旅行中的自然解碼
31 溫迪 J 達比:旅行中的權力圖譜
帕慕克:一個人與一座城
在作家與城市之間,我們經(jīng)常能找到很多生動的呼應,比如狄更斯與倫敦,喬伊斯與都柏林,卡夫卡與布拉格,波德萊爾及其后來者本雅明與巴黎等等。而在帕慕克與伊斯坦布爾之間,這種呼應關系被拉扯得更加濃烈,也更加緊張。不僅伊斯坦布爾被打上了帕慕克的印記,帕慕克也被打上了伊斯坦布爾的印記,我們很難分清這是一座城市的人格化,還是一個作家的街區(qū)地理化,但我們能清晰地感受到帕慕克正以這樣的方式占有了伊斯坦布爾,也一并占有了伊斯坦布爾的歷史和傳奇,而這正是帕慕克的愿望和野心。
在帕慕克新作《我腦袋里的怪東西》的中文版封面上,有一幅帕慕克自己畫的伊斯坦布爾城市地圖,上面畫著一個人——很有可能是帕慕克本人——站在一座高塔上,俯瞰著這座建筑已擠堆得快要跳出來的密集城市,而在這座城市的干凈街道上,一個人也看不到。這座屬于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吸引著無數(shù)的讀者前往那里,但同時它也像一個封閉的“劇院舞臺”,只有待在觀眾席欣賞才最美,因為可以避開丑陋的“舞臺側面”。因此,每個手持帕慕克作品去到伊斯坦布爾的游客,面對帕慕克在這座城市投下的似真似幻的濃稠陰影,理解伊斯坦布爾并沒有變得更簡單,而是更復雜。
帕慕克有一年帶著自己的女兒去黑貝里亞達度假,在馬車氣喘吁吁地拉著他們往山上跑時,帕慕克忽然對那個正像馬蹄一樣躍動著向后退去的世界生出一股懊惱的心緒。“我們一個個仔細審視:一片樹葉,一個垃圾箱,一只球,一匹馬,一個孩子。同樣,我們還能看到,葉的綠,垃圾箱的紅,球的彈動,馬的神情和孩子的臉龐。隨后,每件事物都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我們似乎還未真正觀賞到它們,實現(xiàn)就已經(jīng)移開了。這個午后炎熱世界里的任何一種景物,我們都沒能真正賞析。它和我們擦身而過,仿佛這個脆弱的世界在我們眼前蒸發(fā)了。就連我們也仿佛正在離開自身!我們像是在觀賞,但又像什么也沒看到。”
帕慕克至今已寫了十幾本書,但很少寫到他的旅行,在少數(shù)幾處提到外出旅行的地方,也都像這次黑貝里亞達之旅一樣,出于感受和理解上的不滿足,他的疑惑總是更多于熱情。與之相反,伊斯坦布爾則是帕慕克始終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他自認為生命中一個了解的地方。對這樣一個地方,他不想像旅行者那樣快速地瀏覽,而是試圖用一種生動的手法,去表現(xiàn)它在每24小時所呈現(xiàn)出來的特質(zhì)。
帕慕克的每一本書都試圖在以這樣的方式寫伊斯坦布爾。如果一開始,伊斯坦布爾還只是作為舞臺和布景,越到后來,它就越成為主角本身。《伊斯坦布爾》通常被視為帕慕克寫給這座城市的一封情書,其純真、動人的深情打動了無數(shù)的讀者。《純真博物館》則更進一步,帕慕克把這封情書寫得更浮夸,也更帶有成人的“心計”,小說中這座用來展示“凱末爾和芙頌的真愛”的想象博物館被他隆重其事地搬進了現(xiàn)實,而主角則巧妙地從芙頌嫁接到了伊斯坦布爾。帕慕克用了整整四年的時間去收集這座城市自1970年以來的舊電影票、舊汽車票、舊時伊斯坦布爾官方文件、舊存折,以及人們?nèi)粘I钪惺褂玫乃十嫛⒄掌龋@些搜羅擺滿了83個展柜。而在新作《我腦袋里的怪東西》中,故事本身幾乎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伊斯坦布爾。小說中,伊斯坦布爾被搭成了一種老式的、簡樸的戲臺,小說人物之間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對話,他們挨個進入光束對著觀眾大聲說話、辯解和傾訴,他們是那么親切,似乎讀者正被勾肩搭背引為同謀,他們表現(xiàn)得就像我們外出旅行時希望遇見的那一類城市居民,可以熱情地為我們重演這座城市的歷史和生活。
《我的腦袋里的怪東西》里寫了伊斯坦布爾從1969年到2012年的歷史,小說的主人公麥夫魯特出生于1957年,和帕慕克只相差5歲,他們是同一代人,但并不同屬一個階層。帕慕克在城市里做了很多采訪,拜訪了很多像麥夫魯特一樣的缽扎商人,那些人就像小說中那些熱情的人物一樣也急切地向帕慕克講訴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看見我在那里,所有的80-90歲的缽扎賣家都想和我談談”。在小說中,帕慕克帶著哀嘆和眷念為我們描述了缽扎這種由小米發(fā)酵制成的傳統(tǒng)亞洲飲料:氣味香郁、呈深黃色、微含酒精。因為他認為二三十年后缽扎可能會在伊斯坦布爾消失和被遺忘,一如現(xiàn)在的伊斯坦布爾人不會再像過去那樣把系著繩子的籃子從窗口放下從街頭小販那里買東西。
這是帕慕克頭一次這么完整地講述這座城市里窮人的故事。在上世紀90年代,伊斯坦布爾的人口從一百萬激增到了一千多萬,占到了土耳其人口的六分之一。當我們讀到小說中那些外來移民為了在伊斯坦布爾占得一席落腳之地,我想我們能夠理解他們在城市周邊的山頭上瘋狂建造一夜屋的激情(一夜屋指的是那些在一夜之間蓋起來并入住的屋子,只有這樣,它們才不會被政府制止和拆掉),因為伊斯坦布爾也像我們的北上廣深,它們像巨大磁盤一樣吸引著一代代年輕人趕往那里,有的落下根來,有的被發(fā)配回鄉(xiāng),更多的人則漂浮著,兩頭不著。我喜歡的土耳其導演錫蘭在他的片子中也曾反復觸及這個主題,比如《遠方》講訴的就是一個鄉(xiāng)下人在大都市鎩羽而歸的故事,在他的片子中,去伊斯坦布爾即使一個夢想,也是一種逃離的借口。
這么多人一下蜂擁到伊斯坦布爾,必然也像盲目的洪水那樣在沖撞著這座城市。在《別樣的色彩》中,帕慕克對此似乎有很強烈的抵觸:“如果從上空望下去,你立刻就會明白,為什么家族沖突、貪婪、過失以及自責之情都沒起到什么好作用。你會看到下面的鱗次櫛比的水泥軍團,就像托爾斯泰《戰(zhàn)爭與和平》中的軍隊那樣,一路劫掠所有宅邸、樹木、花園,連動物也不放過,如此強硬、無法遏止;你會看到這支大軍身后,留下的痕跡就是一條條瀝青馬路。這馬路一步步逼近你曾經(jīng)居住的地方,比任何時候都近。而你曾在那里度過仿佛永恒的、天堂般的歲月。……倘若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急劇擴張的無情城市中,那么我們生活在此的房屋、花園以及街巷,那些塑造了我們記憶和自身靈魂的墻垣,就注定會被毀滅。”
在《別樣的色彩》和《我腦袋里的怪東西》之間隱藏的這種情感的對沖,它有點類似于今天也出現(xiàn)在我們生活中的那些有關本地人和外來者之間的長久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有時候雙方看上去似乎有了對彼此處境的理解,都準備表現(xiàn)得寬容,但他們沒有任何一方愿意屈尊被原諒。事實上,與外來移民對城市造成的改變相比,這種相互不休的指責所結出來的惡果,對城市本身的傷害反而更深,一如帕慕克在《我腦袋里的怪東西》中所寫到的那樣:“多年來,小販麥夫魯特已很少被叫去家里。而在二十五年前,幾乎所有人都會讓他進單元房,很多人會在廚房里問他,‘你冷不冷?上午你去上學嗎?要喝杯茶嗎?’一些人還會請他進客廳,甚至讓他坐在他們的桌旁。……在這二十五年里,伊斯坦布爾發(fā)生了太多的變化,以至于這些最初的記憶,對于現(xiàn)在的麥夫魯特來說仿佛神話般。”
城市里這些日益變得“聒噪、活躍、自負的人”致使的人際的變化,恰恰也是帕慕克身在其中每天都在經(jīng)歷的種種,如果小說中的麥夫魯特一直還在“想去適應這些巨變”,帕慕克可能有著更復雜的心緒。在《我腦袋里的怪東西》的中文版封面上,帕慕克在自己畫的伊斯坦布爾城市圖中,依然承續(xù)了曾在《別樣的色彩》中出現(xiàn)的俯瞰視角,他站在一座高塔上,俯瞰著這座城市,并把整座密集的城市歸置得井井有條,而在那些干凈街道上,不分本地人和外來者,都被帕慕克拒絕在了伊斯坦布爾的大門之外。……(完整文章請閱讀《人間旅歷》)
非常滿意 推薦大家購買
很不錯的書,讀來很長知識,很多書中介紹的記者,作家等,他們的經(jīng)歷和人生非常啟迪。
為什么基本信息介紹本書有344頁,目錄里頭有艾科和保羅索魯兩章,可是到手后翻遍全書只有326頁,這二位先生也是蹤跡全無。是出版社編輯問題還是印刷廠漏印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