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jì)無可爭議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V.S.奈保爾代表作
“印度三部曲”第二部,真正理解印度文化的讀本
印度吞噬了自己的文明,在垃圾中生產(chǎn)垃圾,在廢墟中制造廢墟,人民居然能心安理得地生活
本書頗為激烈,但也證明像奈保爾這樣的小說家可以更敏捷、更有成效地指出問題所在,遠(yuǎn)勝世界銀行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以及各種專家。——《泰晤士報》
有一種人遠(yuǎn)離了故鄉(xiāng),卻比故鄉(xiāng)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那里。V.S.奈保爾就是這里面杰出的人。——《時代周刊》
V.S.奈保爾(V.S.Naipaul):
英國當(dāng)代作家,文化巨匠。1932年生于特立尼達(dá)島上一個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進(jìn)入牛津大學(xué)攻讀英國文學(xué),畢業(yè)后遷居倫敦。
50年代開始寫作,作品以小說、游記、文論為主,主要有《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米格爾街》、《自由國度》、《河灣》與“印度三部曲”等。
作品在全球享有盛譽(yù),半個世紀(jì)里,將里斯獎、毛姆獎、史密斯獎、布克獎、及時屆大衛(wèi)?柯恩文學(xué)獎等收入囊中。1990年,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2001年,榮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
及時部受傷的文明
及時章舊有平衡
1
有時的舊印度,那個許多印度人喜歡談?wù)摰墓爬隙篮愕挠《龋坪蹙瓦@樣延續(xù)著。上次大戰(zhàn)時,一些正在接受化學(xué)戰(zhàn)訓(xùn)練的英國士兵在這個國家偏遠(yuǎn)的南部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剎附近駐扎。寺廟里飼養(yǎng)著一條鱷魚,士兵們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射殺了它。他們還以某種形式(也許僅僅是他們的出現(xiàn)本身)褻瀆了寺廟。士兵們很快就走了,英國人也紛紛離開了印度。現(xiàn)在距離那次褻瀆事件已有三十多年,在另一次緊急狀態(tài)時期,寺廟得到了翻修,一座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
在被賦予生命和注入法力之前,這樣的雕像不過是雕刻師院子里的擺設(shè),它們的價值取決于大小、材質(zhì)以及工匠的手藝。印度教偶像來自古老的世界,他們體現(xiàn)著深奧,有時是莊嚴(yán)的概念,而且必須以特定的規(guī)范被塑造。印度教的偶像形象在今天不可能得到發(fā)展,盡管受到印度電影和電影海報的影響,最近的一些形象沒有古代原始形象那么概念化,有種世俗的、玩偶式的美。他們了無生氣、姿態(tài)各異地佇立在雕刻師的展室中。偶爾會有一尊受命而塑的半身像,比如地方警察局的督察之類,他空洞洞的大理石眼睛上可能還會安著一副真的鏡框—這些花崗巖和大理石首先讓人感到置身墓地,或是讓人想起某個備受愛戴的亡者。不過這樣的展室是他們成神之前的過渡居所,每座雕像都等待著被買走、被供奉,這樣他們就有了生命和神性,每個雕像都白璧微瑕,為的是當(dāng)神性生命降臨時不至于太令人恐懼。
所以在曾遭褻瀆的廟宇里,神像必須被賦予生命,要舉行特別的法事,所用的方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種。它把我們帶回宗教和人類奇跡剛剛開始的時候。這就是“道”的方法:太初有道。一個十幾個詞的符咒被吟誦并謄抄五千萬次—這就是在這個憲法被凍結(jié)、新聞遭審查的“緊急狀態(tài)”中,五千名志愿者所做的事。這件事完成后,新偶像下面要放上一塊鐫刻過的金牌,以證明神性之生成以及志愿者之虔誠。千年古剎將重生,印度,印度教的印度,是永恒的。征服和褻瀆不過是歷史中的幾個瞬間。
再往南大約二百英里,巨大巖石的高原之上,是一度興盛的印度維查耶納伽爾王國都城遺址。維查耶納伽爾建于十四世紀(jì),一五六五年被一支穆斯林國家的聯(lián)軍占領(lǐng),并被徹底摧毀。這座城市是當(dāng)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城墻周長二十四英里,外國游客記錄了其結(jié)構(gòu)和精彩程度。毀城行動持續(xù)了五個月,也有說法為一年。
今天,外城已經(jīng)全部成為農(nóng)田,偶爾可見一些磚石建筑的殘跡。通加巴德拉河附近則有更為壯觀的遺跡:一些宮殿和馬廄、一個王家浴池、一座廟宇,里面有一組仍能奏樂的石柱、一道破損的渠以及幾根歪斜的花崗巖柱子,那一定曾是跨河的橋墩。河那邊更多:在一條長長的寬敞的道路的一端,濕婆神巨大的牛頭塑像仍然半面臨街。路的另一端是個奇跡——一座神廟出于某種原因在四百年前的毀壞中幸存,仍然完好并香火不絕。
朝圣者們?yōu)榇硕鴣淼竭@里獻(xiàn)上供品,用古老巫術(shù)進(jìn)行祭祀。維查耶納伽爾的一些遺址已被文物部門宣布為國家紀(jì)念遺址,但對于人數(shù)遠(yuǎn)勝于旅游者的朝圣者來說,維查耶納伽爾既不是它可怕的歷史,也不是它一片荒涼的現(xiàn)在。可知的歷史已經(jīng)淪落為傳奇故事:一位強(qiáng)大的統(tǒng)治者,一個天降黃金建立的王國,那王國如此富庶,珍珠和紅寶石在市場上像谷子一樣地販賣。
維查耶納伽爾對朝圣者而言就是那座幸存的古廟,周圍的破敗就像是古老魔力的證明,正如對過去輝煌的幻想與對現(xiàn)時破敗的接受相調(diào)和。曾經(jīng)繁華的街道(它不是國家紀(jì)念遺址,仍被允許使用)現(xiàn)在是條陋巷。它未經(jīng)鋪設(shè),表面上滿是墨綠色的淤泥和糞便,趿拉著鞋的朝圣者毫不介意地踏過去,走向食品攤和紀(jì)念品店,那里收音機(jī)開著,喧鬧聲震耳欲聾。廢墟上還有占地而居的饑餓的人們和他們饑餓的牲口,殘破的石墻以泥和碎石修補(bǔ),不久前還在門廊上的雕像已被移除。生活24小時天進(jìn)行,往日在延續(xù)。經(jīng)過征服與毀滅,過去的事物重現(xiàn)了。
如果說,維查耶納伽爾現(xiàn)在徒有一個名稱,記得這樣一個王國的人那么少(在二百英里之外的班加羅爾,就有很多大學(xué)生連聽都沒聽說過它),那不僅是因?yàn)樗蝗绱藦氐椎匾臑榱藦U墟,也因?yàn)樗暙I(xiàn)很小,它自身就是過去的再現(xiàn)。王國由一個當(dāng)?shù)氐挠《冉檀蠊谝蝗杲ⅲ荒滤沽执驍『蟊谎褐恋吕铮淖谝了固m教,然后又作為穆斯林政權(quán)的代表回到南方。在遠(yuǎn)離德里的南方,改宗的大公重建獨(dú)立國家,并且不合常規(guī)地打破印度教種姓規(guī)定,重新宣稱他皈依印度教,是當(dāng)?shù)赜《冉躺裨趬m世的代言人。南方的大印度教王國就以這樣的方式成立了。
這個國家延續(xù)了二百年時間,其間戰(zhàn)火未歇。它從建國之始就以復(fù)興已遭破壞的印度教為己任,從文化與藝術(shù)方面來說,它保存并重復(fù)著印度教遺產(chǎn),但很難有創(chuàng)新。其銅雕與五百年前的沒什么差別,即使在當(dāng)時,其建筑與周圍的穆斯林建筑相比也顯得沉重老舊。今天的廢墟坐落于巨大巖石的冷漠風(fēng)景之中,看上去比實(shí)際還要古老,像一處早已被淘汰的文明的遺跡。
維查耶納伽爾所宣揚(yáng)的印度教已經(jīng)走到盡頭,而且已經(jīng)腐朽,它就像風(fēng)行的印度教那樣,輕易地走向了野蠻主義。維查耶納伽爾有奴隸市場,有廟妓。它鼓勵殉夫自焚的所謂圣行—寡婦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以達(dá)圣潔、確保夫家的榮耀并洗清這個家庭三世的罪孽。維查耶納伽爾還以活人獻(xiàn)祭。一次,在建造大水庫時遇到了一些麻煩,維查耶納伽爾大王克利須納?德瓦?拉雅命令用幾個犯人祭祀。
到了十六世紀(jì),維查耶納伽爾簡直就是一個等待被征服的王國。但它宏大而壯美,需要管理者、藝術(shù)家和手藝人。在二百年的歷史里,它必然激發(fā)過土地上的全部才智并將其聚集于都城。王國被征服、首都被有系統(tǒng)地摧毀時,遭到滅頂之災(zāi)的就不僅僅是樓堂和廟宇了:生靈涂炭,王國中所有具備才智、力量和見識的人都被滅族。征服者制造出一片荒漠,這幾乎可說是求敗于人:在接下來的二百年中,亡國之地被反復(fù)蹂躪。
今天,這里仍然顯示著印度教的維查耶納伽爾在一五六五年被損毀的結(jié)局。這個地區(qū)的“落后”眾所周知,看起來這里似乎不存在歷史,很難把它和過去的輝煌甚至大戰(zhàn)相聯(lián)系,在廢墟不遠(yuǎn)處形成的霍斯派特城骯臟破敗,用于農(nóng)耕的田野難有價值。
自獨(dú)立以來,政府向這個地區(qū)投入了不少經(jīng)費(fèi)。通加巴德拉河上建起了一道堤壩,還有一項(xiàng)合并了古王國時期灌溉渠的大型灌溉工程(仍然叫作維查耶納伽爾渠)。一個維查耶納伽爾鋼廠正在籌建中,一所大學(xué)已經(jīng)開始建設(shè),用以訓(xùn)練本地人在鋼廠及隨之而來的附屬工廠任職。重點(diǎn)是對本地人的訓(xùn)練。因?yàn)槟壳斑@塊曾聚集了出色建設(shè)者的土地上人力資源匱乏。本地區(qū)屬于印度聯(lián)邦中一個鼓勵外來移民的邦,這里需要技術(shù)人員和工匠——需要會簡單技術(shù)的人,甚至需要飯店服務(wù)員。余下的只是那些不能理解“變化”觀念的農(nóng)民。就像生氣勃勃的維查耶納伽爾廟外那些在廢墟上占地而居的人,他們在破敗的石墻間穿進(jìn)穿出,像色彩斑斕的昆蟲,在這個下雨的午后吵吵嚷嚷、無事生非。
此次到維查耶納伽爾,站在寬闊的廟前大道上(它看起來已不像十三年前我初次造訪時那么令人敬畏,當(dāng)年那種對神話般的歷史的直率言談也消失了),我開始思考那上千年的侵略與征服注定要給印度帶來的智力枯竭。發(fā)生在維查耶納伽爾的事,不同程度地發(fā)生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在北方,廢墟壓著廢墟:穆斯林廢墟下是印度教廢墟,穆斯林廢墟上還有穆斯林廢墟。史書歷數(shù)著戰(zhàn)爭、征伐和劫掠,卻沒有關(guān)注智識的枯竭,更沒有留意這個國家的智識生活是怎樣的—這個國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xiàn)還是在遙遠(yuǎn)的過去完成的。印度人說,印度從征服者那里吸取經(jīng)驗(yàn),而且比征服者存在得更久。但在維查耶納伽爾,在朝圣者中間,我想知道,是否這一千年來在智識方面,印度不總會在征服者面前退縮,是否在明顯的復(fù)興時期,印度不只是令自己重新變老,在智識上愈發(fā)狹隘且永遠(yuǎn)脆弱。
英國統(tǒng)治時代的這段悲慘的臣服時期,同時也是印度智慧再創(chuàng)輝煌的時期,印度的民族主義宣揚(yáng)印度的歷史,宗教與政治上的覺醒相互滲透與影響。但獨(dú)立后的印度,其五年計劃、工業(yè)化與民主實(shí)踐都讓這個國家產(chǎn)生了變化。在民族為之驕傲的“老”與允諾帶來的“新”之間總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最終令文明產(chǎn)生了斷裂。
這次印度動蕩的起因不在于外國的侵略與征服,而產(chǎn)生于國家內(nèi)部。印度不能再以舊有方式應(yīng)對,不能再退化到古代。她所借鑒的機(jī)制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借鑒機(jī)制的作用;但古代印度無法提供替代新聞、國會以及法院的東西。印度的危機(jī)不只是政治和經(jīng)濟(jì)上的。更大的危機(jī)在于一個受傷的古老文明最終承認(rèn)了它的缺陷,卻又沒有前進(jìn)的智識途徑。
2
“印度會繼續(xù)。”印度作家納拉揚(yáng)一九六一年在倫敦對我說,那時我還沒去過印度。
小說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形式,并不屬于印度的傳統(tǒng),它伴隨英國人來到印度,十九世紀(jì)末首先在孟加拉確立,然后傳播開來。但直到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英國統(tǒng)治末期,才及時次有嚴(yán)肅作家在倫敦出版以英語寫成的作品。納拉揚(yáng)屬于最早的一批,也是好的之一。他從沒成為“政治”作家,甚至在風(fēng)起云涌的三十年代也一樣,他也不像獨(dú)立后的許多作家那樣,認(rèn)為小說和所有的文字作品都是用來為自己樹碑立傳和向世人夸耀的。
納拉揚(yáng)關(guān)注的始終是一個印度南方小鎮(zhèn)上的人,他一本接一本記述著那里的生活。他在印度獨(dú)立十四年后的一九六一年說,不管尼赫魯之后政治如何動蕩,他確信印度會繼續(xù),這很像他在寫于英國統(tǒng)治時期的最早的一批小說里所表達(dá)的信念,那時他說,印度正在繼續(xù)。在早期小說中,英國征服者如同生活中既定的現(xiàn)實(shí),英國人走遠(yuǎn)了,他們的存在卻依然隱藏在他們的體制中:銀行、教會學(xué)校。作家深切思考著那些在底層繼續(xù)的卑微生命:小人物,小伎倆,夸夸其談,意義有限——一個如此受束縛的生命,卻顯示著完整和無損。這種渺小從未引發(fā)過思考,盡管印度本身常讓人覺得廣袤。
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自傳《我的日子》里,納拉揚(yáng)為他的小說填充了背景。這本書盡管內(nèi)容上比起系列小說有所擴(kuò)充,但仍可被認(rèn)為是其中一篇。它并沒有在政治上進(jìn)行探討或給出結(jié)論。南方城市馬德拉斯是英國在印度最早的基地之一,這個據(jù)點(diǎn)由東印度公司在一六四○年向維查耶納伽爾王國的遺民承租,納拉揚(yáng)在那里度過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時光。馬德拉斯所在的這個地區(qū)長期太平,與北方相比更加印度教化,伊斯蘭化程度不高,有著七十五年的長期和平。納拉揚(yáng)說,從克萊夫時代起,那里就不知道戰(zhàn)爭為何物。在及時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巡游的德國戰(zhàn)艦艾姆登號在某夜現(xiàn)身海港,打開探照燈,開始炮轟城市,居民“對漫天星斗的天空突然雷電大作的現(xiàn)象感到驚奇”。一些人逃到內(nèi)陸。納拉揚(yáng)說這一潰逃“跟早些時候的一次遷移行動步調(diào)一致,那次海上突卷暴風(fēng),有預(yù)言說世界將在本日毀滅”。
納拉揚(yáng)童年的世界是一個自得其樂的世界,它把自己變成了一個預(yù)言和魔法的世界,遠(yuǎn)離重大時事,遠(yuǎn)離它能看到的政治可能性。但政治不請自來,而且以可能的方式偷偷地同儀式與宗教相伴而來。在學(xué)校時納拉揚(yáng)加入了童子軍。馬德拉斯的童子軍運(yùn)動由安妮?貝贊特執(zhí)掌,她是個神智學(xué)者,對印度文明有著比多數(shù)同時代的印度人更高的理想;為了迂回地顛覆巴登-鮑威爾爵士的帝國企圖,貝贊特童子軍以《天佑吾王》的曲調(diào)唱道:“主佑我祖國,主佑我貴土,主佑我印度。”
一九一九年的24小時,納拉揚(yáng)參加了一個從伊濕伐羅古廟出發(fā)的宗教游行。隊伍唱著“愛國歌曲”,高喊口號,然后返回古廟,有人在那里分發(fā)甜點(diǎn)。這項(xiàng)喜慶而虔誠的活動是馬德拉斯的及時次民族主義騷動。納拉揚(yáng)沒有提及的是,那其實(shí)是甘地領(lǐng)導(dǎo)的全印度抗議活動的一部分,甘地那年四十九歲,從南非回國三年,在印度還不太知名。納拉揚(yáng)很高興能參加這次游行,但他的一個年輕而時髦的叔叔(印度最早的業(yè)余攝影家之一)卻并不那么想。納拉揚(yáng)說,這位叔叔“反對政治,不希望我誤入歧途。他把所有的統(tǒng)治者、政府和行政機(jī)關(guān)全罵作魔鬼,認(rèn)為尋求統(tǒng)治者的更迭是毫無邏輯的”。
好吧,這就是我們的起點(diǎn),所有四十歲以上、曾居住在殖民地的人,學(xué)會與臣服觀念共生的臣民。我們生活在自己無關(guān)緊要的世界中,我們甚至可以假裝這個世界是完整的,因?yàn)槲覀円呀?jīng)忘記了它曾經(jīng)被打碎。動蕩、不安和發(fā)展都在別處;我們這些戰(zhàn)敗的、遠(yuǎn)離時事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我們在生活中成了被參觀和游覽的對象,一如在文學(xué)中。潰敗而臣服,這使不同的地方變得相似。納拉揚(yáng)的印度及其殖民地體制很像我童年時的特立尼達(dá)。他對于這個體制的婉轉(zhuǎn)看法也和我的一樣。從他小說所表現(xiàn)的印度人的生活中,我發(fā)現(xiàn)了來自世界另一端的那個印度人社群生活的回聲。
但納拉揚(yáng)的小說沒有讓我意識到印度的苦痛。作為作家,他獲得了太大的成功。他的喜劇需要被置于嚴(yán)格的、規(guī)矩分明的社會場景中,他刻畫直接、筆調(diào)輕松,盡管用英語來講述印度風(fēng)情,卻很成功地將異域風(fēng)情寫得平易近人。我知道他虛構(gòu)的小鎮(zhèn)是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為的、簡化的現(xiàn)實(shí)。不過真的現(xiàn)實(shí)是殘酷而迫近的。書里的印度似乎觸手可及,現(xiàn)實(shí)的印度則始終隱而未現(xiàn)。要深入納拉揚(yáng)的世界,要獲得他從印度的缺陷與渺小中所發(fā)現(xiàn)的秩序與連貫,要了解他的諷刺性認(rèn)同并品味他的喜劇,就得無視過多的可見事實(shí),去除過多的自我——我的歷史感,甚至是最簡單的人類可能性的概念。我并沒有失去對納拉揚(yáng)的敬意,但我覺得他的喜劇和諷刺并不像它們所表現(xiàn)的那樣,是印度對世界回應(yīng)的一部分,我對這樣的回應(yīng)已不能認(rèn)同。于是我漸漸清楚了一件事,特別是在這次游歷中慢慢重溫著納拉揚(yáng)一九四九年的小說《桑帕斯先生》的時候。那就是,由于書中所有的人格怪異的歡樂,納拉揚(yáng)的小說不再成為我一度以為的純粹的社會性喜劇,而更接近宗教書籍,還常常是宗教寓言,而且印度教色彩濃烈。
斯里尼瓦斯是《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他是個喜歡沉思的閑人。他做過很多工作—農(nóng)業(yè)、銀行、教育、法律,即印度獨(dú)立前的那些工作,時間是一九三八年—全都辭了職。他待在家宅中(印度大家庭的宅子)自己的屋子里,擔(dān)憂時光流逝。斯里尼瓦斯當(dāng)律師的哥哥照料著宅子,這意味著他照料著斯里尼瓦斯和他的妻兒。斯里尼瓦斯有家,這一事實(shí)與他的年齡一樣令人吃驚,他已經(jīng)三十七歲了。
24小時,斯里尼瓦斯正在屋里讀《奧義書》,他哥哥走進(jìn)來說:“你這輩子究竟想做什么?”斯里尼瓦斯回答:“你沒看到嗎?人生有十項(xiàng)奧義,我要完成它們,現(xiàn)在是第三項(xiàng)。”但斯里尼瓦斯還是接受了暗示,他決定去馬古迪鎮(zhèn)創(chuàng)辦一份周報。他在馬古迪擁擠的街巷里租到一間陋室,洗澡只能用公共水龍頭,又找了一個閣樓當(dāng)報社的辦公室。
斯里尼瓦斯現(xiàn)在入世了,他有了新的責(zé)任和新的人際關(guān)系:房東、印刷商、妻子。(“他自己都奇怪,在這些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幾乎沒注意過她。”)但是他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無為之美。“當(dāng)他對市政或社會的缺點(diǎn)大加撻伐之時,一個聲音一直在問:‘生命、世界和所有這一切都在走向消逝,為什么要煩惱呢?與不都是一樣的。為什么要真的煩憂呢?’”
他的這些沉思看似無聊,而且有種半喜劇性的效果;卻把他推向了更深層的清靜無為的境界。24小時,他在小屋里聽到街上一個女人賣菜的吆喝聲,他先是好奇于她和她的主顧,然后則好奇于每天相遇或沖突的“人的巨大力量”,斯里尼瓦斯感應(yīng)到“生命全景之浩瀚與廣袤”的啟示,于是頭暈?zāi)垦!K耄窬褪窃谶@“全景”中被感知的。后來,他還在這樣的全景中達(dá)到了一種美妙的平衡。“如果一個人能夠?qū)θ诵杂幸环N的理解,那么他也能正確地理解世界:事物沒有特別的對與錯,它們只是在平衡著自身。”已經(jīng)沒必要干涉、沒必要去做任何事了。有24小時和妻子拌嘴之后,斯里尼瓦斯更是輕易地充分理解了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所有形式的非暴力,無論大與小、個人與國家,都注定會在個人和社會兩方面產(chǎn)生一種沒有焦躁和紛擾的安寧。”
但這樣的“非暴力”或“無為”要依靠社會的存續(xù),依靠其他人的“為”。斯里尼瓦斯的印刷商關(guān)了門,斯里尼瓦斯的報紙也就不得不停刊。他通過印刷商(他就是納拉揚(yáng)小說標(biāo)題中的桑帕斯先生)介紹,又成了劇本作者,參與了印度宗教電影的拍攝。斯里尼瓦斯從沒像今天這樣深入這個世界之中,他發(fā)現(xiàn)它喧囂腐敗。純正的思想被弄得一團(tuán)糟,性與鬧劇、歌舞與南美音樂嫁接在印度教神的故事之上。印刷商現(xiàn)在成了制片人,他愛上了女主角。另一個藝術(shù)家也愛上了她。印刷商贏了,藝術(shù)家則發(fā)了瘋。一切都混亂不堪,電影根本沒拍成。
斯里尼瓦斯抽身而退。他找了另一個印刷商,又辦起了報紙,而報紙已不是最初的那種玩笑。斯里尼瓦斯已經(jīng)回歸自身,回歸了他沉思性的生活。有了這層保護(hù)(以及他哥哥資助他的盧比。總是盧比:盧比總是必需的),斯里尼瓦斯就將“成年”看成一種無聊的狀態(tài),沒有純真,沒有純粹的快樂,只有“商業(yè)價值”肯定著無聊的重要性。
還有那個因?yàn)閻邸⒁驗(yàn)樗c這個無聊世界的聯(lián)系而發(fā)瘋的藝術(shù)家。他得接受治療,有個當(dāng)?shù)氐奈讕熤缿?yīng)該怎么辦。人們把他找來,古老的祭祀儀式開始了,并將在對藝術(shù)家儀式性的鞭打中結(jié)束。斯里尼瓦斯想,這些部落成員可能都在公元前十二世紀(jì)出現(xiàn)過。但壓抑的心情沒有持續(xù)多久。想到最初的歷史,他眼前立刻出現(xiàn)了印度幾千年歷史的幻象,以及在他們立足的這塊土地上發(fā)生過的一切事情。
在這片原本是森林的地方,他看到印度教史詩《羅摩衍那》中記載的一個故事正在上演,那本書部分反映了雅利安人在印度開拓定居的情況(大約公元前一○○○年);后來他看到佛陀安慰一位失去孩子的婦女時說:“請從沒有亡靈的家中帶一把芥菜籽來給我。”還有哲學(xué)家商羯羅查爾雅,他宣講吠檀多至印度各地,一次看到一只正產(chǎn)卵的青蛙在其天敵—眼鏡蛇的庇蔭中躲避日頭,便建了一座寺廟。然后歐洲的傳教士來了,同行的還有商人和士兵,以及街那頭英國銀行的經(jīng)理席林先生。
“朝代興衰,宮殿和樓廈時現(xiàn)時隱。整個國家在侵略者的火與劍之下垮塌,在沙拉育河泛濫時被洗凈。但它總能夠重生和成長。”與此相比,一個人發(fā)瘋又算什么?“發(fā)瘋一半都因?yàn)樽约旱男袨椋驗(yàn)樗狈ψ灾驗(yàn)樗撑蚜嗽o自己一片馳騁疆場的藝術(shù)家本性。他遲早會擺脫瘋癲,展現(xiàn)自己真實(shí)的本性——盡管不能在一世,而至少是在幾世之中??瘋癲或健康、痛苦或幸福看起來都一樣??在‘永恒’的沖刷之下,沒有什么是了不得的。”
所以藝術(shù)家在遭鞭打時,斯里尼瓦斯沒有介入;后來當(dāng)巫師要求把藝術(shù)家抬到一座偏遠(yuǎn)的寺廟、在門廊外放上一個星期時,斯里尼瓦斯覺得,藝術(shù)家在這期間是否得到照顧無關(guān)緊要,甚至是死是活都無所謂。“就算瘋癲過去了,”斯里尼瓦斯在他的精神喜悅中說,“只有存在肯定著其自身。”
粗讀歷史,然后情感上認(rèn)定印度的永恒和生生不息,隨之而來的并不是對未來被打敗、被毀滅的恐懼,而是一種漠然處之的態(tài)度。印度總會眷顧自身,個人不必承擔(dān)任何責(zé)任。在這種廣義的漠然中還有對朋友命運(yùn)的漠然。斯里尼瓦斯得出結(jié)論,把自己看作藝術(shù)家的保護(hù)者才是發(fā)瘋。
V.S.奈保爾將深具洞察力的敘述和不受世俗侵蝕的探索融為一體,迫使我們?nèi)グl(fā)現(xiàn)被壓抑歷史的真實(shí)存在。——諾貝爾文學(xué)獎頒獎辭
今天,甘地主義既不起政治作用,也不起社會作用,甘地主義今天擁有的只是“妄想”而不是“思想”。——蘇德哈?雷
本書頗為激烈,但也證明像奈保爾這樣的小說家可以更敏捷、更有成效地指出問題所在,遠(yuǎn)勝世界銀行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以及各種專家。——《泰晤士報》
奈保爾的寫作優(yōu)雅,,一針見血。——《新聞周刊》
一段走到“亂象”背后的印度之行,一部充滿智慧、直擊要害的杰作。——《華盛頓郵報》
典型奈保爾風(fēng)格:犀利、簡潔、焦慮,在感性的底色中蘊(yùn)藏著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堅強(qiáng)。——《紐約時報》
準(zhǔn)備好好看看此類書,了解平時不太關(guān)注的知識點(diǎn)。長長見識。
這本書感覺還可以i,就是字太密,沒有讀下去的沖動。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總該沒敏感詞了
內(nèi)容很棒,書不錯。但說實(shí)在的,還是三聯(lián)的老版本手感好,精致小巧。這個硬殼精裝手感差點(diǎn)。
了解下印度,不光是風(fēng)土人情,文化最能表現(xiàn)一個民族。
他國文明借鑒學(xué)習(xí),購書量大未及細(xì)讀,總體不錯。
V.S.奈保爾(V.S.Naipaul): 英國當(dāng)代作家,文化巨匠。1932年生于特立尼達(dá)島上一個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進(jìn)入牛津大學(xué)攻讀英國文學(xué),畢業(yè)后遷居倫敦。50年代開始寫作,作品以小說、游記、文論為主,主要有《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米格爾街》、《自由國度》、《河灣》與“印度三部曲”等。 作品在全球享有盛譽(yù),半個世紀(jì)里,將里斯獎、毛姆獎、史密斯獎、布克獎、第一屆大衛(wèi)?柯恩文學(xué)獎等收入囊中。1990年,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2001年,榮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
同一批買回來的書中只有這一本沒有看完,書籍還是很不錯的,可以毫無保留的說這是一部值得閱讀的作品。看完之后再追評。
代人購買,無法真實(shí)評論,但看推薦語非常值得一看的樣子。版形偏小,顯得不夠大氣。
前時讀了奈保爾溜達(dá)伊斯蘭教地區(qū)的《在信徒的國度》,回頭才發(fā)現(xiàn),還是印度三部曲最贊,屬于奈保爾真正的代表作。前一本《幽暗國度》里他悲觀,只看到滿街就地拉屎的人。這一本里,他毒辣,難過,因?yàn)樗豢吹健霸谌魏螘r候任何人在一個小坎口面前,都往宗教里找原因”。我突然想到了一個詞:中世紀(jì)。上帝究竟有三個牙還是五個牙?到圣經(jīng)里找證據(jù)。無聊之極。但文字不多的一本書,卻是很沉,很沉。
這的確是奈保爾《印度三部曲》中最薄的一本,但個人覺得其思考深度更犀利大膽,本書是由1975年印度總理、國大黨主席英迪拉·甘地下令宣布終止憲法、進(jìn)入“緊急狀態(tài)”開始的——讀完本書我恍然大悟,這是有象征意義的,因?yàn)閲簏h和甘地淵源極深,今天的國大黨多少是甘地的政治遺產(chǎn),而本書正是要批判甘地思想的繼承者的不足之處。 這是很艱難的!因?yàn)樵凇队陌祰取分校伪杽倓偢叨荣澷p了甘地那源于二十年的南非經(jīng)歷所具有的一般印度人不具備的視野,現(xiàn)在就要進(jìn)一步指出其思想繼承者的不足——奈保爾真是個鋒利的人! 本書所反映的印度正處于工業(yè)化時期,所以《幽暗國度》…
不知道是內(nèi)容偏向政治社論還是翻譯問題,比起第一本《幽暗國度》略顯枯燥乏味。
書很不錯,內(nèi)容也值得期待,是為了解印度的國民性而買
當(dāng)當(dāng)網(wǎng)上購書幾年來最讓人驚喜的一次,因?yàn)橄胭I的書和已經(jīng)買了的書太多了,實(shí)在是看不過來。留在以后看完后再來補(bǔ)充評論。
印度這個神奇的國度,一直以來都特別感興趣,但是也一直打怵不太敢去,先通過書籍了解一下吧。
大師關(guān)于印度的作品不少,這是三部曲之一,值得一看。
奈保爾的書,作為純文學(xué),還保持了暢銷作家的流傳性。
讀完《幽暗國度》就來接著收印度三部曲的第二部啦!文明失落的靈與肉,挫敗國度的亂象背后,原來竟是這樣的深不可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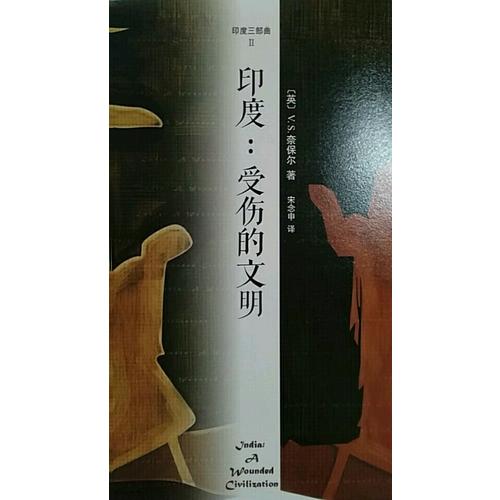 期待有人寫一部《中國:受傷的文明》。雖然時代已經(jīng)變化,但是經(jīng)典之所以經(jīng)典在于他洞徹了你我看不到的東西,社會、人性不會過時。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總要有一個局外人點(diǎn)醒局內(nèi)人。
期待有人寫一部《中國:受傷的文明》。雖然時代已經(jīng)變化,但是經(jīng)典之所以經(jīng)典在于他洞徹了你我看不到的東西,社會、人性不會過時。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總要有一個局外人點(diǎn)醒局內(nèi)人。
近期對印度文化特別感興趣,一口氣買了印度三部曲,想了解這個同樣神秘的國家。
買這本書是用來湊齊印度三部曲的。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終于收齊了。
嘿嘿,奈保爾在最開始其實(shí)很幽默的。印度三部曲不光能讓人了解印度,還能一窺奈保爾的脾性。非常喜歡。
印度三部曲,是最喜歡的奈保爾作品,當(dāng)然,還包括《米格爾街》。現(xiàn)在迷上了奈保爾的印度。和真實(shí)的有所區(qū)別嗎,想知道。
為了了解這個神秘的國度,翻開印度三部曲。到底是種姓制度還是宗教造就成印度。而今天的印度又是什么樣子?有沒有什么會被顛覆,亦或本質(zhì)從未被改變。期待第三部
印度三部曲之一,可以對印度這個特別的國家了解一些。
這本書是奈保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以前看過多本他的書,很喜歡他的風(fēng)格,喜歡他的作品里的歷史感。從本質(zhì)上來說,奈保爾是個文化的背叛者,但是他同樣是文化的梳理者,他對印度的批判其實(shí)就是以歐洲文明為榜樣的構(gòu)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