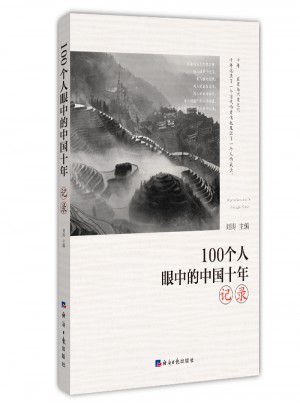
100個人眼中的中國十年·記錄
- 所屬分類:圖書 >文學(xué)>紀(jì)實(shí)文學(xué)
- 作者:[劉濤]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9787802579569
- 出版社:經(jīng)濟(jì)日報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6-06
- 印刷時間:2016-06-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shù):--
- 紙張:純質(zhì)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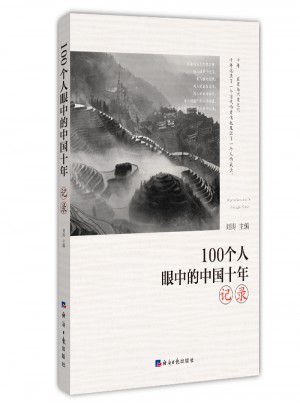
本書選擇100來個普通中國人,借助新聞特寫的體裁樣式,致力于呈現(xiàn)100個中國人近十年的生命故事和命運(yùn)遭際。在人物命運(yùn)的深層結(jié)構(gòu),是中國十年的巨大轉(zhuǎn)型和變遷。本書勾勒出一個有關(guān)中國十年的基本圖景,有助于人們了解并把握這十年中國的變化。
劉濤,暨南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暨南大學(xué)環(huán)境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暨南學(xué)報》(CSSCI)新聞傳播學(xué)欄目主持。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環(huán)境傳播、視覺修辭、媒介文化。主持國家/省部級課題6項,獨(dú)立發(fā)表SSCI/CSSCI論文30余篇,獨(dú)著《環(huán)境傳播:話語、修辭與政治》獲教育部第七屆高校科研成果獎(人文社科)二等獎,廣東省哲學(xué)社科成果獎一等獎。曾任央視《新聞?wù){(diào)查》策劃/編導(dǎo)(2005-2007),作品獲中國廣播影視大獎專題一等獎。目前兼任《中國教育報》簽約評論員,開設(shè)評論專欄,作品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三等獎。
目錄
序
十年 記錄疼痛
解凍十四年
父與子,暗黑中的漂浮止于何時?
早婚,抹不去的疤
二十年家暴
一個母親和她的肌肉萎縮癥女兒
十年 喧囂之外
采訪公益律師廖建勛
石炳坤:工人維權(quán)的護(hù)航人
我用筆桿為你維權(quán)
“聽話”的生活——人在富士康
十年 生生不息
白首不改當(dāng)年夢
心有多大,就去走多遠(yuǎn)
與國畫的美麗邂逅
萬物有靈且美,且將這美永恒
烏蘭巴托土地上的華夏情
十年 漫步陽光
航拍楊星興
站到光亮中去
十年堅守防控艾滋病及時線
巴索風(fēng)云的“垃圾情結(jié)”
俠客亦溫情
“狗媽媽”與她的“孩子”們
醉心公益
一路荊棘,痛并快樂
李可樂和他的伙伴
十年 來時的路
外科醫(yī)生說“醫(yī)患”
鐵打的軍營流水的兵
黑暗中的列車守護(hù)者
胡雅君:采訪在熱愛中繼續(xù)
細(xì)膩的心,雕琢細(xì)膩的美
一個單親媽媽的守望
不要命的偏執(zhí)狂——陳龍
何真:生命的堅守
余月香:接生三十余年
新聞線
十年 不安的心
一個獨(dú)立攝影師的自由
不如歸去
孤獨(dú)的凝望
生命的擺渡人溫暖與感動常在
一半情懷,一半生意
生命營救融化冰山喚醒愛
選秀歌手的“以前”與“后來”
看藝術(shù)喚醒美
十年 萬家燈火
何全淑:城市傷疤里的住客
千里馬的傲氣
兩代人的尷尬
盲人奶奶的風(fēng)雨學(xué)醫(yī)路
農(nóng)民工何景光和他的奮斗史
遷往新疆最北部
五十而退
20年里好的答案
我只是千萬人中普通的一個
你們長大了,我們就老了
十年
十年 記錄疼痛
“記錄疼痛”,傾聽最底層的聲音。事物相生相克,有陰必有陽,有喜必有悲。有人過著幸福的生活,也有人生活得并沒有那么幸福。記錄疼痛,也許我們依舊無能為力,但讓更多人看到真實(shí),這本身又何嘗不是一種改變?
買來的越南新娘
細(xì)芬,是她現(xiàn)在的名字,19年前,她從越南被拐賣到了中國,成為一個陌生人的新娘。
如今的她40歲了,中等身材,偏白皮膚,一頭燙發(fā)扎在后腦勺,看起來比實(shí)際年齡年輕了一點(diǎn)。她常常把笑容掛在嘴角,開口說話時,聲音中略帶著南方女性特有的溫婉,似乎還帶著歡快的悅動。這使得他人自然而然地認(rèn)為,她是生活的眷兒,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人。
然而,聽到她的故事,很多人都嚇一跳;和她相識后,便會漸漸欣賞這個積極而樂觀的女人。
命運(yùn)失控了
21歲之前,細(xì)芬一直生活在越南的一個小村莊里,家里有5個姐妹和2個兄弟,自己排行老三,父親是一個高中教師,然而薪水并不高,一家子過得緊巴巴的。21歲那年,細(xì)芬高中畢業(yè),可遺憾的是,她就差幾分沒能考上大學(xué)。懂事的她知道家里的難處,并沒有選擇復(fù)讀。和父母商量后,她決定和同鄉(xiāng)的幾個姑娘一起到城市里去打工,她萬萬沒想到,自己這一去,竟要相隔14年才再一次回到這個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才再一次見到自己的父母,她更沒有想到,這種以前在故事里才能聽到的事情,竟然降臨在自己身上。
那是開始打工的半個月后,細(xì)芬已經(jīng)和周圍的人漸漸熟悉起來。有24小時,廠里的一個小伙子約細(xì)芬和其他幾個年輕女工友一起去城里逛逛。到了城里,小伙子便說要上廁所,讓她們在原地等候,然而過了很久仍不見蹤影。姑娘們有點(diǎn)著急,這時候來了一個陌生人。他說小伙子和她們錯開了,接著還好心地帶她們?nèi)フ遥蛇€是找不到小伙子。
陌生人很無奈,讓她們在原地等待便離開了。姑娘們照做了。
之后又來了一個陌生人,以同樣的理由帶走了她們。那時候她們還察覺不到異樣,只是覺得氣憤,“好好的一日游卻變成了尋找同伴。”可是善良的姑娘們還沒有放棄尋找,她們覺得,既然一起出來玩,得一起回去才好。
可是萬萬沒想到,這竟然是一場預(yù)謀已久的騙局,這個她們一心尋找的伙伴,竟然就是出賣她們的人。
傍晚的時候,在毫無防備之間她們被告知,自己已經(jīng)被賣給了眼前的這個人。“我要的是錢,你們別想逃跑,不然性命不保。”眼前的陌生人略帶威脅。
細(xì)芬還來不及對眼前的狀況做出一個反應(yīng),她甚至以為自己還在做夢。可是接下來的幾天,使她明白,自己正在經(jīng)歷的,是噩夢一般的現(xiàn)實(shí)。
她們隨即被人販子用車運(yùn)走。后來,從人販子和司機(jī)的對話中細(xì)芬隱隱約約知道,自己會被帶去中國。
“那時真的好慘。”盡管多年過去,對這段記憶,細(xì)芬仍歷歷在目。人販子每天只給幾個女孩子每人一包方便面,僅僅只夠維持生命,饑餓一直折磨著她們。為了掩人耳目,所走的都是僻靜的路,崎嶇顛簸,一個人也沒有。人販子卻還是怕被人發(fā)現(xiàn),時不時地恐嚇那幾個女孩子。她們一點(diǎn)聲音都不敢發(fā)出來,不然就會被打。
“我們根本就沒有求救的機(jī)會。”細(xì)芬那個時候已經(jīng)絕望。除了絕望外,還有一種對前方無知的恐懼,會被送到哪里,會去做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敢想。有24小時晚上,她聽到人販子和司機(jī)的對話,“今晚這一站,過得去就一起賺錢,過不去就在這幾個中間選一個送給你。”
大家一聽到這個消息,更在原來的恐懼中增加幾分無措,仿佛無論怎么走,前方都是鬼門關(guān)。
沒有愛情的婚姻
后來,誰也沒有被送給司機(jī),都來到了中國。細(xì)芬被賣給了一個素未謀面的潮州男人當(dāng)媳婦,和當(dāng)初的幾個姐妹也斷了聯(lián)系。
對于自己的這段經(jīng)歷,對于自己的異國身份,細(xì)芬并沒有對他人隱瞞。然而講到她的丈夫,那個用8500塊錢,便買斷了她的青春她的一切的男人,她卻常常避而不談。即使偶爾談到,她也一直用“孩子的爸”來稱呼,仿佛兩人間的聯(lián)系只有孩子。
用8500塊錢,便使兩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瞬間變成枕邊人。語言不通、同床異夢,是他們最初的狀態(tài)。如今,細(xì)芬已經(jīng)在中國生活了19年,環(huán)境將她塑造成了一個完全的潮汕媳婦,但是,卻沒有改變這對“老夫老妻”的狀態(tài),即使細(xì)芬如今已經(jīng)能夠順暢地講潮汕話,即使他們已經(jīng)有了三個孩子。甚至,因細(xì)芬的工作地點(diǎn)離家里比較遠(yuǎn),她干脆在工廠附近租了一間房子,自己一個人住在那里,有空的時候就回去看看孩子。
“想過一走了之嗎?”
“想過啊。”可是……
細(xì)芬沒結(jié)婚前就有過這樣的念頭。那時她在這段“婚姻”的中間人家里住了半個月。這家女主人也是“越南新娘”,熟悉的語言使細(xì)芬錯以為找到了救星。她哀求女主人借給她8500塊,她想贖回自己。可是,女主人無奈地拒絕了。“在那個時候,8500塊實(shí)在太多了”,細(xì)芬不怪這個同病相憐的女人,“她也是沒有辦法。”
在現(xiàn)實(shí)壓迫下,細(xì)芬妥協(xié)了。異國他鄉(xiāng),身無分文,她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走不了。
半個月后,簡單的本地結(jié)婚儀式過后,甚至連結(jié)婚證也沒有,細(xì)芬就從一個少女變成一個少婦。
四五個月后,細(xì)芬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
一年后,她的及時個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兒!初做母親的她,一顆心已經(jīng)被孩子牽絆住了。后來,細(xì)芬相繼有了第二、第三個孩子。
為了孩子,細(xì)芬決定不走了。
“渾渾噩噩的,就過去了這么多年。”在這段買賣的婚姻里,愛情成了奢侈,孩子是她的牽掛。
積極向前看
細(xì)芬決定在中國也要活得開心些。“總要往前看的嘛”,她說。
所謂“日久見人心”,可還沒一起生活多久,細(xì)芬就發(fā)現(xiàn)丈夫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丈夫不出去工作,細(xì)芬不得不把工作扛在自己肩上,從結(jié)婚沒多久就這樣。“細(xì)芬不容易啊,一旦廠里活少了,她就要重新?lián)Q個活多點(diǎn)的服裝廠,家里都靠她”,細(xì)芬曾經(jīng)的一個同事表示。
可是細(xì)芬對于現(xiàn)狀還是相對滿足的。她靠自己的努力,讓自己過得挺好,除了那段無愛的婚姻。但這非但沒有把她禁錮住,反而使她更積極地去尋找生活中的亮點(diǎn),她一直在積極地融入新生活。
開始的時候,是細(xì)芬最難熬的階段,不通的語言,如陌生人的“家人”使她有些不知所措。為預(yù)防她逃跑,總有人看著她。細(xì)芬每天就呆在家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后來,征得家人同意,細(xì)芬到村里的服裝廠打工,這才使得她和外界有了聯(lián)系。細(xì)芬很聰明,幾個月間便大致聽得懂潮汕話的日常用語,但是只能用手比劃著來表達(dá)自己的意思。同時,她也勇于開口,盡管有時會引來同事的笑聲,她總是會回一句:“那應(yīng)該怎么講?”就這樣,她越講越流暢,一兩年后,她就基本能夠講潮汕話了。學(xué)會了當(dāng)?shù)氐恼Z言,細(xì)芬就像找到了和外界溝通的橋梁,和同事間的友誼,使她在無愛的婚姻里找到了安慰。
細(xì)芬并不止步于學(xué)潮汕話,生活中,她珍惜一切機(jī)會學(xué)普通話,看電視的時候,她跟著電視學(xué),平時在工作中,和同事學(xué)著講。然后,她自己嘗試著用手機(jī)發(fā)短信,近幾年,細(xì)芬的手機(jī)中還下了QQ、微信等社交軟件,有空的時候就會玩一玩,好友大多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就這樣,在娛樂的同時,字越認(rèn)越多,普通話交流也基本沒問題了。
說起現(xiàn)在的生活,細(xì)芬滔滔不絕。她說這幾年比較開心的事情,一個是大女兒去年考上了市里的一所重點(diǎn)高中,另一個,就是在2010年的時候,她終于回了趟老家。
細(xì)芬在中國的前十年,一直沒有和家里聯(lián)系。經(jīng)濟(jì)的壓力以及被騙的陰影使細(xì)芬沒有去尋找回家的路。直到2006年,廠里來了一名越南的工人,細(xì)芬一問,竟然是老鄉(xiāng)!細(xì)芬很激動,在老鄉(xiāng)回去的時候托他送去了一封家書。至此,細(xì)芬和娘家人才算聯(lián)系上了。“整整十年了!及時次打電話時,我連越南話都不會講了,只能聽著”,細(xì)芬說。
2010年,細(xì)芬才再一次踏上越南的故土。“十四年了!”她感慨道。
“家里人都很好,父母還健在,經(jīng)濟(jì)狀況也比以前好多了。”細(xì)芬很開心,但是由于中國的家里小女兒還小,她只停留了半個月就趕回來了。細(xì)芬有些不舍,“只能希望多賺些錢,多回去幾趟看看父母。”
細(xì)芬是一個愛美的人。盡管工作很忙,還要經(jīng)常性晚上加班,但這并不妨礙細(xì)芬打扮自己。除了買些價格能夠承受的衣服,她前段時間還去美容院辦了一個療程的臉部保養(yǎng)。每天,細(xì)芬都會以好的狀態(tài)出現(xiàn)在同事面前。
但是,細(xì)芬一直以來有一個煩惱,就是她的身份問題。“有時就在想有身份證該多好,目前我就像黑戶一樣。”這幾年村領(lǐng)導(dǎo)也有通知細(xì)芬和村里幾個有相似經(jīng)歷的人去拍照,說是可以辦了,但是到頭來總還是辦不成。不過她又慶幸孩子的身份證等都沒問題了,在升學(xué)上沒有需要擔(dān)心的。
“聽說其他地方有人已經(jīng)可以辦了。”細(xì)芬相信,自己有24小時也能辦成功,成為一名真正的中國公民。
采訪結(jié)束時,細(xì)芬正準(zhǔn)備和同事一起去唱K,“難得沒有加班,放松下心情。”
命運(yùn)變了軌道,細(xì)芬在努力活得更好。
(黃妙哲)
解凍十四年
凌晨四點(diǎn),房間里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呼吸聲。
剛合上眼的王莉靜趕緊一個轱轆,從地鋪上爬起來。丈夫侯勇全身一點(diǎn)兒也動彈不得,平躺在床上,呼吸不過來,憋得滿臉通紅。王莉靜很熟練地用力把他的身子翻到一邊。側(cè)著躺下的侯勇終于平靜下來。
王莉靜夜里每十分鐘都要給侯勇翻一次身。為了方便照顧他,她在床頭下面的小空地上鋪了一層棉絮,打起了地鋪。
這地鋪一躺就是三年。
“再難受就叫啊。”王莉靜把被子扯直,蓋住侯勇的腿。
他輕輕“哼”了一聲,表示回應(yīng)。
明早還有課,王莉靜躺下來,趁著空隙趕緊瞇一會兒。
天塌了
王莉靜和侯勇都是運(yùn)動員出身,兩人高中就在一起了。她考上武漢體育學(xué)院那年,他分到廣州體育學(xué)院工作。
四年來,兩個人的戀情都靠書信維持著。快到畢業(yè)的時候,王莉靜開始糾結(jié)要不要回老家工作。
“可是一個人對我好,我就不去想那么多,一畢業(yè)就跟來了。”她對我說。
來到廣州后,剛踏入社會的兩個年輕人擠在一間不足20平米的小房子里,地方小得放下一張床都會堵。天氣潮熱,地面上霉菌叢生,大塊大塊的白灰從墻壁上跌落下來。
抱著兩歲大的兒子,王莉靜背靠著殘舊斑駁的墻壁,拍下了許多老照片。這些照片記錄了她最快樂的日子。
2000年,侯勇單位分了套大房子,兩口子換了新房。
王莉靜很羨慕以前的日子,雖然住的小,但是很快樂。現(xiàn)在房子大了,老公倒下了。
2001年,侯勇被確診肌萎縮側(cè)索硬化癥(俗稱漸凍人癥)。
誰也沒料到這種病會被侯勇攤上。出生于體操世家的他,多次體操比賽獲獎,是著名運(yùn)動員李小雙的隊友。墻上的一張老照片還記錄著他握緊吊環(huán),側(cè)空翻時“騰空”的瞬間。
可是如今,他卻像被冰雪封凍住一樣,喪失了任何行動能力。
14年前的24小時,侯勇發(fā)現(xiàn),他的腿突然不如平常那樣聽使喚了。雙腿總是抬不起來,就好像不是他的一樣,根本不跟著他走。沒辦法,他只能拖著腿,一點(diǎn)點(diǎn)地向前移。這種情況剛開始只是偶然出現(xiàn)。沒想到一次網(wǎng)球比賽上,他突然摔倒,半天才能爬起來,雙腿像從前那樣靈活就更難了。
心急如焚的侯勇趕緊去了醫(yī)院。跑了好幾家,醫(yī)生都說找不準(zhǔn)問題,要他住院觀察。
侯勇有點(diǎn)慌,王莉靜是個小女人,很多事情都依靠著他,這件事絕不能讓她知道。于是他白天住院,晚上就跑回來睡覺。一段日子下來,王莉靜竟然一點(diǎn)兒也沒有察覺。
直到有24小時她在房間里打掃衛(wèi)生時,突然發(fā)現(xiàn)了一張丈夫的檢查報告,上面畫了個問號。
王莉靜頓時慌了,打電話給侯勇,連忙趕去醫(yī)院。
當(dāng)著他們的面,醫(yī)生說,小伙子,該吃吃,該喝喝,該玩就玩,你的壽命只有兩年。
漸凍人癥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怪病,在全球每90分鐘就會奪走一名患者的生命。這種病的原因至今不明,也沒辦法治療。
而最讓人難以承受的是,這些癥狀的變化都是在病人大腦清醒的狀態(tài)下發(fā)生的。也就是說,病人會非常清晰地看著自己一點(diǎn)一點(diǎn)痛苦地死去。
在我國發(fā)病率僅有十萬分之四的絕癥竟然發(fā)生在侯勇身上,一家人覺得像遭到一場天災(zāi)。
“我感覺天都要塌了!”這個連陰天打雷都怕的女人抱著兩歲的兒子,懵住了。每天能做的就是哭。
“我從小到大都是運(yùn)動員,運(yùn)動員除了運(yùn)動,什么都不懂。來到廣州之后什么都是他來做。他走了,我怎么辦?”
王莉靜幾乎不能跟人提起丈夫的病情,話還沒到嘴邊淚就涌出來了。每天眼睛都是紅的,沒有課的時候,她就坐在辦公室里哭。
那段時間,垮下來的她一下子瘦了好多。
一閉眼,什么也不用管了
“我們沒有想過放棄。”
夫妻倆從2001年開始,全國各地先后跑了很多地方。
兩人先去了河北石家莊一家專治漸凍人癥的醫(yī)院。三個月的療程下來,沒有一點(diǎn)效果。
無奈他們又跑去貴陽找土方子,租住在一個老中醫(yī)家里。
王莉靜因為還要回學(xué)校上課,只能讓她爸爸和弟弟從老家趕過來輪番照顧。
可是親人的接力并沒有減緩冰凍的速度。
“你頂著!只要有這個藥,無論多少錢,哪怕把房子賣了,我住橋洞,都要治。”王莉靜拖著一瘸一拐的侯勇四處找偏方,經(jīng)常上當(dāng)受騙。
“錢花了,人更慘了。”
2004年,王莉靜決定不再帶侯勇到處尋醫(yī)了。連火車都坐不了的他很難再經(jīng)得起天南地北的奔波。
回到廣州,夫妻倆想起結(jié)婚時沒有拍紀(jì)念照。于是,王莉靜抱著兩歲的孩子,攙著瘸著腿的丈夫,在附近的照相館拍了張一家三口的婚紗照。照片裱好后就一直放在房間的床頭邊。
相片上,穿著一襲婚紗的王莉靜依偎著西裝革履的侯勇,他的臉因為打了激素,看起來很圓潤。
脫下婚紗,她又穿回一身黑衣服。自從侯勇生病,再也無心打扮的王莉靜每天都是“黑色的”。
一身的黯淡藏著絕望。
此時的王莉靜悄悄為自己安排好了未來。
“他走的那天,就是我走的那天。”
望著家屬院旁邊較高的那一幢樓,她想象著自己慢慢走上去。站在天臺上,仿佛閉著眼向下一跳,什么也不用管了,再也不用痛苦了。
他們趕不走我
王莉靜越想越不對勁,她在日記本里寫道:“如果我一走掉孩子就成孤兒了,他該怎么辦;對爸媽來說,最殘忍的就是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公公婆婆再沒了媳婦,肯定會倒下。”
“一個人自私,會影響到大家。”這句話是用紅筆寫的。
不想一直籠罩在悲傷情緒里的王莉靜開始在網(wǎng)上搜一些心理學(xué)的資料看。偶爾路過書店,她會進(jìn)去挑幾本喜歡的買回去讀。《人性的缺點(diǎn)》、《心理與生活》等書現(xiàn)在還存放在辦公桌的柜子里。
王莉靜告訴自己,眼淚并不能解決問題,哭得再多也沒用。老公是個病人,都一直在咬著牙堅持,她怎么能天天哭哭啼啼,尋死覓活的。
至此,她再也沒了輕生的念頭。
沒想到自己剛剛想通,丈夫就開始趕她走,公公婆婆也來勸離婚。
王莉靜喂侯勇吃飯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丈夫不像從前那么“懂事”了。他會把剛喂進(jìn)去的飯吐得她滿臉都是,喝水也吐在她臉上。她委屈得受不了,我那么全心全意照顧你,還要帶孩子,你反倒不理解。
她不愿當(dāng)著家人的面哭出來。趁著晚上洗澡,憋了許久的眼淚順著浴頭的水終于傾瀉下來。
紅著眼睛的王莉靜慢慢平靜下來,坐在沙發(fā)上開始琢磨侯勇的反常。
“他這是在逼我走。”
第二天早上,侯勇又吐了王莉靜一身。她用毛巾抹了下臉后,把碗重新端起來,對侯勇說:“你要么繼續(xù)吐,要么就吃。”
侯勇見這樣沒效果了,干脆把嘴閉著。王莉靜就陪著他,你不吃我也不吃,我們就餓著,看誰先倒下。侯勇看著心疼,見她不吃飯,只能張口要她喂。
,誰也趕不走她。
來了,面對
丈夫倒下以后,王莉靜成了家里的支柱,帶孩子,照顧老公,還要堅持上課,慢慢學(xué)著獨(dú)當(dāng)一面。當(dāng)初那個黑色的小女人,慢慢有了些光彩。
這樣下來,堅持了14年。
家里聞不到一點(diǎn)藥味,因為她每天都要給丈夫洗洗沖沖。侯勇身上已經(jīng)沒有肉了,全是骨頭架子,坐在馬桶上會比較疼。所以她就把他抱在臥室的凳子上,給他洗頭,擦身子。
“他還用洗面奶呢。”王莉靜笑著說。
中午下班回來,王莉靜放下東西,先去用力親下她的“大兒子”,伸手抱一抱他。
在他們家,她有兩個兒子,侯勇是他的大兒子。
給“大兒子”做飯是個技術(shù)活。
王莉靜把飯菜用高壓鍋壓好之后,放在小鍋里,再放些剁碎的青菜重新煮。由于侯勇的舌頭大部分都萎縮了,連嚼的力氣都沒有,有時候還需要把飯在絞肉機(jī)中絞成糊。
“病人也是要換口味的,他喜歡我做的東西,”王莉靜很得意,“他覺得有口味的時候,會一直笑,嘴巴張得很快,一勺子進(jìn)去,笑得口水往下流。”
“你看,大家都說我喂飯的時候像玩雜技的”。王莉靜很有興致地從手機(jī)里翻出一張照片。
照片上,王莉靜抬起腿,用雙腳支撐著侯勇的頭,然后一只手拿著碗,另一只手用勺子把飯伸到他嘴里。有的時候,飯會順著口水從嘴角流出來,王莉靜就趕緊放下碗,拿毛巾去擦拭。
“別看他臉圓圓的,身上都沒有肉了。其實(shí)最痛苦的不是我,是我老公”。
如今的侯勇全身基本上都萎縮了,交流只能靠眼珠。他平時喜歡在電視上看網(wǎng)球比賽,王莉靜就去買了個大電視掛在墻上。她又做了一大張紙,上面寫滿了每個頻道,貼在墻上。王莉靜用手指著紙上的頻道,侯勇對他眨眼。眨一下,就是這個臺;眨兩下,就接著換。
每當(dāng)有比賽的時候,兒子就陪著侯勇一起看。父子倆愛好非常相似,是網(wǎng)球運(yùn)動員費(fèi)德勒的球迷,還都喜歡打籃球的詹姆斯。侯勇用力擠著喉頭深處的肌肉,發(fā)出微弱的聲響,眨著眼睛一點(diǎn)點(diǎn)向兒子解說比賽的狀況和技巧。這是他的教育方式。
2004年以后,侯勇就一直呆在那個小房間里,十幾平方米就是他所能看到的世界。為了不讓他和社會脫節(jié),王莉靜沒事就坐在床邊陪侯勇聊天,講講學(xué)校發(fā)生的事情。
夫妻倆一個說話,一個眨眼回應(yīng),卻有說不完的話。
“有時候生活就是這樣,來了,面對。”她很平靜地對我說,又像是在告訴自己。
“別動!”王莉靜拿著手機(jī)對準(zhǔn)角度點(diǎn)下“錄像”。“以后不在了,放著看,留個念想。”對著鏡頭,侯勇很開心地笑,努力嘗試著做很多動作。他的動作主要就是笑,眨眼睛,笑得口水順著嘴角流下來。
活著
王莉靜有個習(xí)慣,沒事愛寫點(diǎn)東西。
自從侯勇生病起,她都會把每天的心情和感觸記錄下來,存放在電腦的一個文件夾。以后老公不在了,翻翻自己從前的狀態(tài),看看那時候是怎么面對的。
“生活中沒有一個人,一生沒有坎坷;沒有一個人,一生一世沒有痛苦。”王莉靜的辦公桌上貼著一張寫滿話的便利貼。
平時看到有幫助的話她就摘抄下來,中午閑下來就翻出及時條開始看。一旦往不好的方面想,就拿出來開導(dǎo)自己。
“得這種病的人,也就是兩三年,像我老公的病友,基本上都走了。”她對我說,“活著,家就是完整的。”
對王莉靜來說,最幸福的就是侯勇還活著。
她想要的很簡單,只要每天下班后,他的眼神還和她交流著。
可是這個簡單的要求卻需要十幾年的堅守。
14年來,王莉靜沒有請過護(hù)工。照顧自己的愛人,是做老婆應(yīng)該做的。
這些年操勞下來,她的身體狀況并不好。
已經(jīng)年近四十的王莉靜有著很嚴(yán)重的骨質(zhì)增生。疼得厲害的時候,她讓兒子使拳頭用力打,打麻木了就不疼了。她的股骨頭也有問題,走路基本上靠腳尖,腳跟無法落地。最怕的就是變天,全身關(guān)節(jié)疼得她徹夜睡不著覺。
“我睡覺都是跪著睡,要么就是趴著,反正不能躺;有時候疼了,半夜就開始捶。”
她和侯勇商量,為自己買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險,以后不給兒子添負(fù)擔(dān)。
“這都是命!”經(jīng)常有人這么對王莉靜說。
“我不信!別人都說好人有好報,老天爺會照顧好人,”剛開始她會很激動,“我出去的時候會對著天空說,老天爺我不信你,我老公那么好的人,為什么要他得病!”
如今,她更不信命。有病了就去治,治不了就盼著,看能不能出現(xiàn)奇跡。
最殘忍的事
三年前,王莉靜的父親罹患肝癌去世。
“我這個人現(xiàn)在再怎么樣也不會哭,但是談到我父親……”王莉靜捂住嘴,不想讓自己哭出來,可是眼淚卻一串串地往下掉。
因為要照顧侯勇,父親臨終前,王莉靜回去了一個月。
20多天里,父親什么也沒吃,她也吃不下。
“我父親走的時候眼睛是睜著的,清醒的,他是餓死的,不是疼死的。”
走之前,父親的手放在她手上,說了句:“很不放心你。”
這個最懂女兒的人,生前一直讓她不要放棄。
父親走,對王莉靜來說是最殘忍的事。
她不禁想到侯勇。
不敢去想,可是又止不住:“他眼睜睜地看著你,什么都是清醒的,沒了,沒有呼吸了。”
這是王莉靜及時次直面自己最親的人死去。
“我面臨了一次,還要面臨第二次,老天爺太殘忍了。”
那段時間,睡不著的時候,她會閉著眼睛,想想侯勇真的走了該怎么辦。
父親走了之后,王莉靜終于振作起來,敢去面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死亡。
從前,在兄弟姐妹中這個最幼小的,現(xiàn)在反而成了最堅強(qiáng)的。
幾年下來,王莉靜一直在試著調(diào)整自己,“我要把好的一面給他看到。”
我是彩色的
“老師,你今天好酷!”
華成小學(xué)的操場上,一群小學(xué)生笑嘻嘻地站成一排,鼓著掌迎接他們的老師。
<